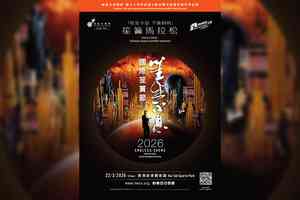「當老師打電話過來,我發現他叫我女兒是He,我立刻糾正:『我女兒是She,不是He。』」
阿寧語氣平靜地回憶起那年女兒13歲,當學校以男性代詞稱呼女兒時的第一反應。作為單親媽媽,她知道女兒正進入青春期的探索階段,但這突如其來的轉變,仍讓她心中掀起波瀾。
「我沒有發脾氣,只是觀察她的反應。」她說。女兒沒有反駁,也沒堅持己見,「當我否認她是He時,她也沒跟我爭吵,表示這中間還有空間可以移動。」
阿寧,這位生活在紐約的母親,陪著女兒走過了一段性別認同混亂與情緒崩解交織的青春時光。她不急著否定,也不盲目附和,而是以母親的耐心與愛,一點一滴將孩子從青春期混亂的邊緣拉回現實,直到女兒走出自己的低谷。
黑色三年:從混亂到蛻變的陪伴
青春期不只是性別探索,更是身體與心理的劇烈變化期。最早出現的是情緒與生活細節的潰堤。
「她不是突然變成那樣的。」阿寧早在幾個月前就察覺,女兒情緒低落、作息紊亂,還開始強烈排斥自己的身體。「那時候她會用繃帶去裹著自己的胸部,就是不想讓身體發育得像個女生。那是疫情期間,我帶她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診斷她有性別認知障礙。」
「她在亞馬遜買那些東西,我當然氣,但我能怎麼樣?我只能告訴她:你想穿可以穿,但如果不舒服就要脫掉,因為這些東西可能會影響你的發育。」語氣不帶批評,只講事實。
情緒崩潰的日常也不容忽視。「她可以一個禮拜不刷牙、不洗臉、不洗澡,房間亂得像垃圾場一樣,把自己關起來。我甚麼辦法都沒有。外公外婆天天嘮叨她,但我知道罵沒用,那個時候她已經是worry depression(焦慮型抑鬱),情況很嚴重。」
強硬逼迫只會帶來更大對立。阿寧選擇每天站在房門外,輕聲說:「要不要洗個澡?晚上會睡得比較舒服喔。」不責備,只提醒,「你只能從她的角度出發,讓她知道你站在她這邊。」
但家庭內部也充滿張力,尤其是代溝與文化觀念的碰撞。
「我好不容易勸她出來洗澡,我媽媽卻忍不住說了句:『好好的一個女孩子變成這樣,沒光了。』這句話就把我所有努力全打回原點,女兒啪一下把房門又關上了。」
愛,是穩住孩子的靈魂
阿寧坦言,女兒當時的穿著與打扮常讓她尷尬:「她一身黑衣、頭髮遮住臉,和人群格格不入。我站在她後面,真的倒吸一口涼氣,覺得很丟人。」但轉念一想,她自問:「如果連我都嫌棄她,那誰能接納她?」
「說實話,她有些打扮我也真的接受不了,從心裏也會有反感。但我知道,這個時候該閉嘴。」阿寧學會不在第一時間反駁,而是找對的時機和女兒討論:「你為甚麼會喜歡這樣的打扮?」
阿寧說,最難的是「代入對方角度」進行溝通。她明白,若情緒壓不住,就會傷人;只有穩住情緒,才有機會拉近彼此距離。每當遇到看不慣的情況,她都提醒自己要放下情緒,並不斷告誡自己:「想想你要的最終目標是甚麼。比起丟人,更重要的是她還活著,還願意跟我出門。」
這段旅程沒有捷徑,為了理解孩子的行為與狀態,阿寧大量閱讀心理學書籍、看電影、研究青春期的各種變化與特質。「我現在非常關注精神健康,不只是孩子的,也是我自己的。」
學校來電催作業,她也堅持自己的判斷:「我說,她的問題不是功課,是精神健康。今天逼她寫,明天她崩潰了怎麼辦?」
在美國養孩子,面對的不只是文化差異,還有制度風險。她語重心長地提醒:「千萬、千千萬不要動手打孩子。」
她分享,最近她認識的一位媽媽因為周六晚上打了孩子,結果孩子離家出走,在地鐵裏被警察發現。警察問發生甚麼事,孩子說媽媽打了他,結果兒童福利局介入、對媽媽提出刑事起訴,孩子被帶去寄養家庭。
「這類案子在我們社區裏一直都在發生。尤其是14歲上下的孩子,一旦被帶走,要回來真的很難,因為很多孩子已經不願意回來了。」阿寧說,「孩子叛不叛逆,其實是取決於你們的關係。不能壓制孩子。我們那一代父母,習慣的是壓制、服從。但現在的孩子不一樣了。」
這三年間,阿寧不斷面對挑戰與試探。「她有時會在一大桌親友面前突然問我:『如果有一天我找了女朋友,你會怎麼想?』」阿寧明白,這是孩子在試探她的邊界。
儘管內心翻江倒海,她仍努力保持冷靜,回應道:「那是你的選擇。」但她也不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你要知道,在亞洲家庭裏,這種事真的很難被接受。你這條路,會走得很辛苦。」「我愛你,我會努力去理解、去嘗試接納,但有時候,我也會控制不住。這不代表我不愛你,而是我也有我的難處。」
性別探索浮動,媽媽要穩
性別認同與情緒波動交錯出現,是這段歷程中最複雜的一部份。
「現在這個時代的問題是,孩子高興的時候感覺自己是She,不開心的時候又變成He。這個性別認同是浮動的。」阿寧說,這讓她學會不再執著於代名詞,而是直接用女兒的名字稱呼她;她與其他青少年交往時,也儘量避免會「踩雷」的問題。
這些變化,與社群媒體影響密不可分。
「現在的孩子在網上看太多性別相關的影片。很多影片會告訴你:你感到抑鬱,是因為你不是你現在的性別。」阿寧說,女兒也曾一度把「性別」當作逃避情緒痛苦的出口。
而教育體系普遍傾向「尊重學生的性別自我認同」,對家長而言更是兩難。
但作為母親,她選擇穩住自己、穩住家。「你要冷靜,想清楚你真正的目標是甚麼。」她說,女兒也曾用「自殺」來威脅她的情緒,「但我學會了不被牽著走」。
三年,不只是救了孩子,也是救了自己
「很多家長只把孩子送去心理諮詢,自己卻不參與。錯了,家長要一起下場。」
阿寧堅持,陪伴不是控制,也不是把責任交給專業人員,而是和孩子一起走過低谷。三年來,她從未強迫孩子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而是一步步學習放下控制、接納現實。
隨著時間推移,女兒不再否認自己是女生,開始重新打扮,主動完成學校功課。老師打電話來報喜,「我女兒真的不一樣了。」她笑著回憶女兒問她:「你為甚麼不像其他媽媽那樣催我成績?」她的回答很簡單:「因為我活過來已經不容易,你活著比甚麼都重要。」
守住那條可能回頭的路
「如果我在這個階段,還是那種暴躁的媽媽,一直逼她改、逼她服從,最後會怎樣?可能就真的把她逼上絕路。因為那是我的想法,不是她的。」
阿寧說,孩子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自我探索的空間,而不是被控制與否定。這三年,她學會與孩子「有商有量」,從對立走向理解,「這個時代已經改變,父母必須更強大,才能穩住孩子的靈魂。」
這不僅是母女之間的對抗與和解,更是一場她與自己童年創傷、與家族疾病史的深刻對話。她大量閱讀心理學書籍,學習觀察孩子的情緒起伏與生活作息的變化。同時,她也親身走過焦慮與憂鬱的黑暗時期,才能在女兒最混亂的時候穩住自己,成為她最堅實的依靠。「如果你不願面對,就很可能錯過拯救孩子的機會。」
這段經歷或許無法成為所有家庭的範本,但在變性議題日益敏感、父母角色日益邊緣的今天,阿寧的選擇,提供了一種值得思考的視角——當世界鼓勵孩子快速定義自己,父母是否還能守住那條「可能回頭的路」?
「那是一段混沌的青春期,就像《混沌少年時》這部片的名字一樣。你只要陪她走過去,孩子會醒來的。」阿寧說。#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