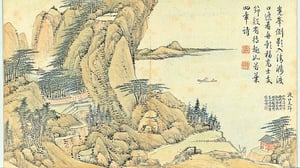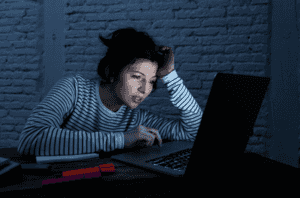英國著名作家C.S.劉易斯(C.S. Lewis,1898—1963)在其開創性的三章體隨筆《人類的廢止》(也譯為《人之廢》,The Abolition of Man,1943)中,通過虛構人物蓋烏斯(Gaius)和提修斯(Titius)來諷刺當時的道德相對主義者(moral relativists)。他尖刻的批判揭穿了他們的道德宣言不過是權宜之計而已。
該書的第一章「沒有胸膛的人」(Men Without Chests)抨擊了那些只是在做宣傳的所謂「教育家」(educators)以及他們的「綠皮書」(Green Book),這是劉易斯對道德相對主義者書籍的蔑稱。第二章則譴責道德相對主義者是所謂的「創新者」(Innovators)。當然,與第一章一樣,他也是在諷刺。
修正道德價值觀
劉易斯批評那些譴責他所說的「道」(the Tao)或自然法則、傳統道德、第一原則或第一柏拉圖(First Platitudes)的所謂「創新者」。他還說,創新者在試圖修正神聖的道德價值觀時,既不能完善也不能取代這些價值觀。在尋求社會「毀滅」(destruction)的過程中,他們並不像他們假裝的那樣主觀。他們的懷疑是膚淺的。他們樂於用懷疑的態度去質疑別人的價值觀,卻認為自己的價值觀不容挑戰,更遑論揭穿。
創新者通過「不批准」(disapprovals)和「批准」(approvals)來表明甚麼是他們不可以接受的,甚麼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他們的標準不是原則,而是是否符合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勇敢或騎士精神是無稽之談或虛無縹緲。他們讚揚那些要和平不要戰爭的人,但卻不關心如何維護和平,即使在和平需要先發制人或進行防禦性對抗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們樂於享受道德價值或準則的果實,卻不願意付出代價去獲得這種果實。
在劉易斯看來,只有在「道」的範圍內行事,人類的尊嚴才能達到應有的標準。
劉易斯特別提到了「黃金法則」(The Golden Rule),他解釋了所謂「創新者」是如何武斷地蔑視殉道(martyrdom)精神,無論是為國家還是為上帝殉道,都被他們蔑稱為「非理性」(irrational)的情感。對他們來說,除非「對社會有用」(useful for the community),否則殉道毫無意義。然而誰來決定甚麼是有用的呢?既然「創新者」摒棄了民族自豪感或榮譽感等客觀價值,他們就不可能明白這樣的簡單邏輯:除非有人冒險赴死,否則所有人都得死。
那麼,為甚麼只有一部份人會死?於是,創新者們以本能為藉口尋求庇佑。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受本能約束,為甚麼還需要「綠皮書」的勸誡呢?如果一種本能是有效的,那麼其它所有本能不也是有效的嗎?如果不是,誰來決定本能的等級?創新者傲慢地試圖避免訴諸「任何更高的法庭」(any court higher),從而最終使自己陷入困境。
無論是基督教(Christian)的「不可作偽證」(Do not bear false witness),還是儒家(Confucian)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like them to do to you),最崇高的道德準則早已流傳下來。而這些道德準則與本能——一種物種「不加思考」(unreflective)的衝動——毫無關係。
沒有任何原始衝動堅持要求我們信守承諾、珍視生命、克制性衝動或暴力衝動。要求人服從於本能,就如同要求要聽命於任何人一樣,都是徒勞的。人言人殊,本能亦是如此。為甚麼對一個人的服從要勝過對另一個人的服從呢?同樣,本能也是如此。向一個人點頭,你必然會毫無意義地向「無盡的本能倒退」(endless regress of instincts)點頭。
在劉易斯看來,是我們人類,是我們獨特的人性,為我們各種相互衝突的本能賦予了相對的尊嚴,使我們可以超越享樂主義(hedonism)和自我保護(self-preservation)等本能。如果我們不這樣做,我們就會一直是野蠻人;我們的原始本能就會一直是原始的,我們就沒有得到教化。
孔子主張「道」(the Tao),基督主張真理是「道」(the Way),而不是眾多方法中的一種。在劉易斯看來,這並不意味著傳統道德(東方和西方、基督教、異教/Pagan或猶太教/Jew)應該是不可動搖的。然而,這些批評必須在道和真理的框架內具有建設性,而不是憑空捏造。
詩人或劇作家從一種語言中挖掘出他們的天才;他們根據語言本身的條件來處理語言,就像作曲家一樣,在音樂的語法範圍內工作,豐富音樂,而不是顛覆音樂。那麼很自然,對於創新者來說,基督教和儒家關於同理心(empathy)的教條就是荒謬的。
相比之下,德國哲學家尼采(Nietzsche,1844—1900)式的創新者不受「道」的約束,是一堆矛盾的詞藻。他們非但沒有通過參透「道」的精神來協調「道」在文字上的差異,反而攫取一條戒律,然後將其駕馭「至死」(to death)。
看看新時代的創新者們都幹了些甚麼。
女權主義的歪曲
女權主義(Feminism)的出發點可能是合法的,即讓女性投票,讓女性更好地與男性一起參與公共生活。然而許多女權主義者最終把女性描繪成超人類(superhuman),把男性描繪成次人類(subhuman),使兩者都偏離了正常的人類軌道。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是無可指責的優越者,而男性則是無可救藥的劣等人。這樣的認識就像通過冥想提升思想,卻用迷幻藥腐蝕身體一樣,是自取滅亡。
現在,女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傳染病,它撕裂了婚姻、家庭、親子關係、童年等神聖的制度,並將劉易斯所預言的許多反常現象注入社會。美國迪士尼(Disney)電影公司在翻拍經典影片《白雪公主》(Snow White,2025)時對原著材料的摒棄,說明了事情可以變得多麼變態。
女權主義的極端形式是尋求消滅男人或消滅人類;厭男症(misandry)滋生厭女症(misogyny),而厭男症和厭女症又滋生針對彼此的仇恨。
真理在於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而非其人為造成的表象。《聖經》中的墮落天使之所以墮落,是因為他們幻想自己超越了自己。男人和女人也一樣,當他們想像自己比實際更強大時,他們自然就會墮落。
計劃生育也許是有計劃的,但它開始實施的時候是為了生育嗎?它建立在享樂主義的基石上,而享樂主義也推崇離婚、單親和墮胎,以及無視性別差異的現實而進行新的性別建構。
享樂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道」,它把邪惡說成是善良,把魯莽說成是權利。墮胎和變性生態系統被偽裝成生殖或性「保健」(healthcare),而放任則被偽裝成全面的性「教育」(education)。
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的凱瑟琳‧馬赫(Katherine Maher)曾不無諷刺地說,有「不同的真相」(different truths)。創新者通過將真相的質地和色調進行扁平化,從而可以自如地說謊。
不同的人可能會有高矮胖瘦之分,膚色或黑或白之別。然而,對於創新者來說,只有某些形容詞相當於「身體羞辱」(body shaming),而其它形容詞則是公平的描述。在「正面接受身體」(body positivity)的旗幟下,醜陋的東西都被宣稱為美麗。有影響力的人士將顯而易見地把不健康的肥胖和厭食症奉為偶像。
真正的道德進步是讓道理變得更清晰,而改變只是在混淆概念。進步是完善舊的框架,而非全盤否定。
讓我們來看看現在的人們對承載著「道」的同理心和自我犧牲等價值觀的習語的反應吧。
15世紀到17世紀全球航海時代,大家都說「婦女兒童優先」(Women and children first),這是「道」在古代以他人為中心的思想的改進和推進版本。而現在的另一個習語「人不為己天誅地滅」(Every man for himself)則否定了這一點,取而代之的是更新的生物進化論的成語「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
不,犧牲並不是航海時代或中世紀的發明。它借鑑了更古老的法則。「婦女兒童優先」將早期的關愛他人的號召延伸到了更脆弱的他人身上。它使進化的本能超越了自我保護。體格更好、更強壯的人有更好的生存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必須只有他們才能生存下來。
這種文明精神世代相傳。它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地步:在自然災害中,救援人員通常不會只關注婦女和兒童,而是理所當然地關注孕婦、病人、老人和殘疾人等弱勢群體。
然而,今天的創新者更傾向著眼於特定的膚色、種族、民族和性別,根據這些特點來貼上的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標籤,精心挑選那些他們認為更有價值的人。實際上,「創新者」是在製造受害者。
更高的道
儘管「道」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但它並不一定是一成不變的,也不一定要求人們毫無疑問地服從。劉易斯承認,它時不時需要進行一些改革(而且不需要一些矛盾)。然而即使在這裏,批判的「方式」也很重要。他警告說,只有尊崇「道」的人才能推進「道」。
基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明確指出,他來不是要廢除摩西律法(the law of Moses),而是要完善它、實現它。他希望他的聽眾不要撕毀律法,而是超越律法的文字,將自己與律法的精神聯繫在一起。
對基督而言,「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適合信仰中孩童般不成熟的人;舊約時代的人們對上帝的理解尚不成熟,因此對他們自己的理解也不成熟。
然而,對於成年人或信仰上更成熟的人來說,「不可殺人」的道德標準太低了。基督將其提升到了更能反映人類真正尊嚴的高度。他提供的不僅是一種新的道德,而且是一種更高尚的道德,要求他的追隨者擁抱敵人,而不僅僅是忍受敵人。
有了這個更高的清晰度,「不傷害」(Do no harm)這個古老但仍適用於現實生活的格言似乎就足夠了,是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還遠遠不夠。
這就是「道」的實際作用。「道」推進道德規範,而不是改變道德規範,同時為人類指明方向,引領人類前進,無論如何,這個作用總是積極向上的。#
作者簡介:
魯道夫·蘭伯特‧費爾南德斯(Rudolph Lambert Fernandez)是美國的一名獨立作家,主要撰寫流行文化方面的文章。
原文:The Way’: C.S. Lewis, on the Only Way of Being Huma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您希望我們報道哪些藝術和文化主題?請將您的寶貴想法或反饋通過電子郵件發送至: features@epochtimes.nyc。
----------------------
♠️中美關係藏暗湧♦️
1️⃣ 美國境內的秘密戰爭
https://tinyurl.com/bdhrdnt7
2️⃣ 跨國鎮壓技倆一覽
https://tinyurl.com/4xst7r2d
3️⃣ 評論:習近平實權暗地移交 新決策層如何抉擇?
https://tinyurl.com/3c8h2d9n
----------------------
【不忘初衷 延續真相】
📰周末版復印 支持購買👇🏻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