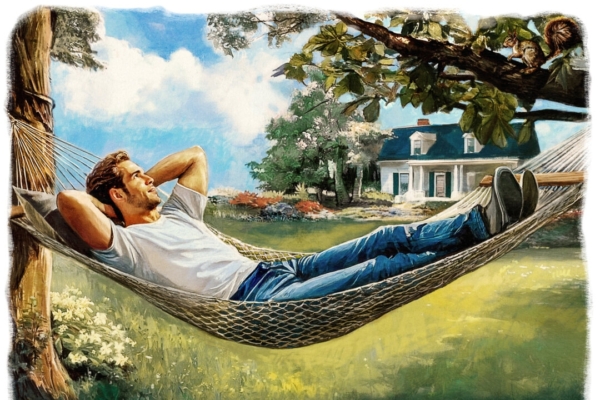「Il dolce far niente」——「無所事事的美好」。這個意大利短語對很多人來說會較為陌生。當待辦事項清單比藍鯨還長時,甚麼也不做又有甚麼美好可言呢?無所事事不僅會耽誤我們完成任務,還要求我們處於不受刺激、不投入、甚至無聊的狀態。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面對自己的思緒,並且沒有多巴胺的介入——顯然,這個想法讓我們害怕:一項心理學研究發現,67%的男性以及25%的女性寧願給自己施加輕微電擊,也不願獨自坐著思考哪怕15分鐘。
仔細想來,我們確實整天都在逃避無聊。手機似乎正是為這種「逃避」而打造。我們指尖觸及的,是無盡的數字世界:頭條新聞、電影、播客、文章、遊戲、社交媒體、短訊等等。74%的美國人不習慣將手機留在家裏,71%的人在新一天開始的頭10分鐘便會查看手機。
當我們感到無聊時,多數人會立刻投向這個小小數字伴侶的懷抱尋求慰藉。但我們真的應該這樣做嗎?
「無聊」對大腦有益
許多思想家和研究者認為,我們不需要總是逃避無聊。事實上,無聊在人類健康心理中起著重要作用,也對人們的生活本身至關重要。它為大腦提供了急需的休息,同時打開創造力的閘門,促進自我認知與反思,並教會我們深刻體會到「存在」,而非僅僅是「做事」。
人類的大腦從不休息。我們進行的每一項活動都需要大腦付出努力,這些腦細胞相互之間以及與身體其它部位進行無休止的交流。只有在夜間睡眠時,大腦才得到一些緩解,思緒也得以理清。
但即使在清醒時,大腦也需要休息的時間。一張持續拉滿的弓最終會磨損,並失去力道和彈性。正如布賴恩‧羅賓遜(Bryan Robinson)在《福布斯》雜誌中所提到的,無聊通過為大腦提供所需的放鬆而有助於其健康。此外,無聊對於社交改善一樣有所助益,因大腦在這種狀態下更易處於開放、樂於交流的默認模式。
無聊中的美
研究人員和創意工作者都發現,無聊還能激發靈感。羅賓遜解釋道:
「無聊實際上會激發創造性想法,重新填滿日漸枯竭的創意儲備並恢復你的工作動力。在那些看似無聊、空洞且無意義的時刻,長期潛伏於腦中的策略和解決方案得以被釋放並實現。」
詩人、劇作家和散文家亞倫‧安傑洛(Aaron Angello)親身體驗了這一點,他給自己設定了一項不尋常的寫作任務:連續114天,每天清晨早起,坐在同一把椅子上,面朝前方,花約30分鐘思考莎士比亞《第29首十四行詩》中的一個單詞。換句話說,他每天早上都會讓自己陷入短暫無聊的狀態。隨後,他開始寫作,一直不停,直到填滿整頁紙。最終,他寫成了一本書,名為《記憶的事實:114回沉思與虛構》(The Fact of Memory: 114 Ruminations and Fabrications)。安傑洛回憶道:「現在回想起來,我意識到自己偶然發現了令我最富成效的寫作方法之一。」
在其散文《沒有無聊就沒有創造力》中,安傑洛將自己的寫作體驗比作困在火車上的人們,他們處於最適合白日夢和頭腦風暴的狀態:
「身體雖仍處於以往位置(坐著,面朝前方),但大腦通過擺脫對日常中一連串無關緊要事務的持續參與,使得當事者能從有意識的思維侷限中走向我所稱的『超意識』思維的廣闊領域。在火車上(或巴士上,客廳的椅子上),我們從參與瑣碎事務的狀態轉向一種可以稱之為無聊的狀態,而這種狀態正是進入創造性的通道。」
許多卓越的詩人、發明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在從事某些與工作無關的事情時常會有「靈光一現」的時刻。傑弗里‧戴維斯(Jeffrey Davis)在為《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撰文時強調了這一點:
「在一系列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被要求完成單調、令人感到無聊的任務時,受試者往往會在之後表現出更高的創造力。無聊是一種『驅動多樣性的情緒』,意味著它促使我們去尋找新的、不同的——因此具有創造性的——體驗和解決方案。無聊能自然地培育出好奇心和開放性等基礎特質,對於新體驗和環境持更開放的態度,進而帶來更多潛在的創造性洞察。」
他建議充份利用日常中自然出現的無聊時段,例如通勤和午休時間,且不要通過屏幕來即刻逃避這些閒散的思緒。
獨處的靜謐時光
除了作為創造力的催化劑,無聊還通過獨處的氛圍促進自我反思以及自我認知。
我們常害怕獨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隨之而來的寂靜和無聊。然而,孤獨與寧靜對於處理和總結經驗至關重要,也通過這些經驗總結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自己。這也正是人類建立自我認知的途徑。
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在其著作《重拾對話:數碼時代的溝通力量》(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中寫道:「孤獨是人們發現自我的地方,並幫助與他人建立真正的連結。當我們缺乏獨處的能力時,我們會依賴外界以期減少焦慮或讓自己感到活著。」
那些長期依賴外部刺激——無論是社交、數碼設備,亦或兩者兼有——才能在自身狀態中感到舒適的人,可能並沒有很強的自我認知。而學會處於當下、探究過去和未來,則需要對一定時期的無聊狀態保持開放。這些無聊時刻是通向思維的門戶;它們引導我們進入未計劃、意想不到的思考軌跡。
特克爾進而生動地闡述道:「要重獲獨處的能力,我們要學會將無聊的片刻視為向內探索的理由,並且至少在某些時候能夠推遲『去別處』。」這種避免總是「去別處」的態度,恰恰對應著一種「活在當下」的意願。接受短暫的無聊——甚至是無聊的威脅,讓我們能體會到此刻並關注眼前的世界。
我不久前也親身體驗到這一點:當時我被困在一個沒有網絡訊號的地方,等待接送。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活在當下。結果,這段經歷成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我事後反思道:
「在無任何電子設備干擾,遠離城市數英里,又無法加快妻子到來的情形下,我別無選擇,只能獨自守在溪邊。這是一種幸福的無力感。時間同時放慢了。我從行動的領域進入了純粹存在的領域。我不是『某個試圖完成任務的人』,也不是『去別處的人』。我只是一個偶然降臨於存在的人,偶然發現了眼前的世界,那一刻它如此鮮活地呈現出來,令人驚歎於它的美麗精巧。」
為無聊留出時間
羅賓遜還認為,我們應該有意在一周的日程中安排這樣的時刻。他建議,不僅僅制定「待辦事項清單」,還應製作一份「存在清單」(to-be list)。存在清單為練習正念、留意當下留出時間:
「你給自己留出空隙,在會議之間伸展身體、深呼吸;留出時間繞街區散步、清理思緒;或是冥想、祈禱、練習椅子瑜伽,看草慢慢生長,或只是思考宇宙。當大腦與這些無所事事的時刻共處,它會更健康、快樂。」
在日程表上,很少有人會在某個時間段裏寫下:「無所事事」或「感受無聊」的簡單備註。然而,如果我們更多人這樣做,個人生活以及整個社會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無聊促使我們去傾聽並敞開心扉。當沒有事物衝擊著我們的注意力,沒有任何「娛樂」佔據著我們時,我們便獲得了自由——即使這種自由伴隨著些許痛苦和初期的不適。我們可以向世界開放自己。正如特克爾所說:「你不必離開房間。坐在桌前傾聽即可。你甚至不必傾聽,只需等待,學會安靜、平靜、獨處。世界將自由地在你面前呈現,讓你得以揭示其本真。」◇
原文:The Sweetness of Doing Nothing: Why We Need Boredom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