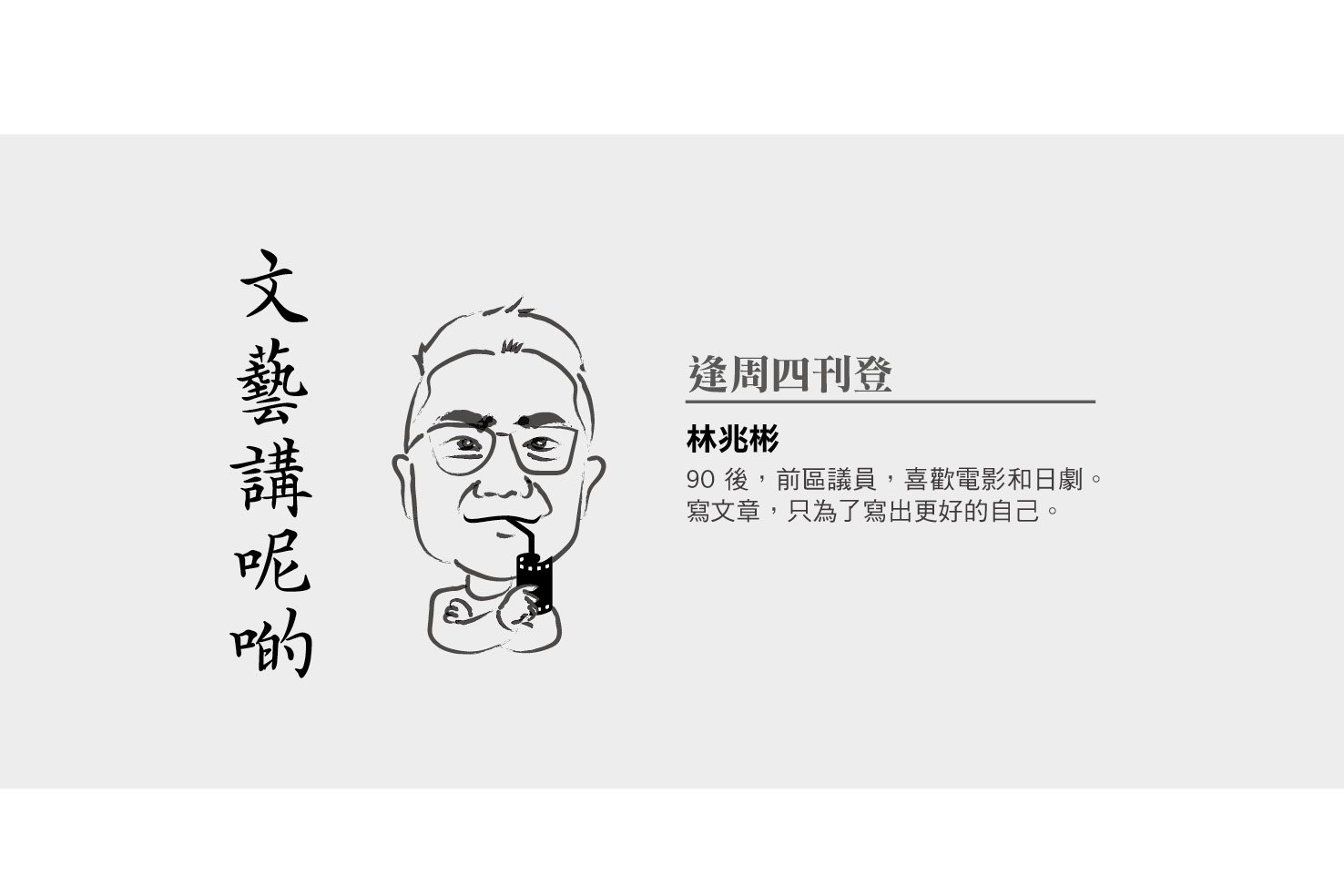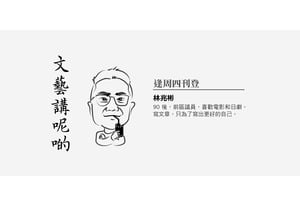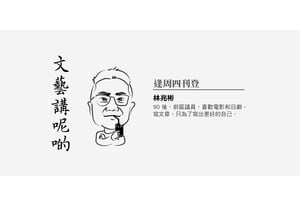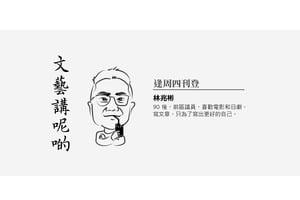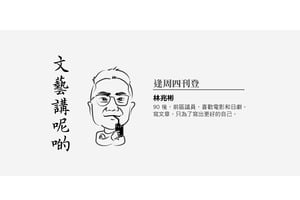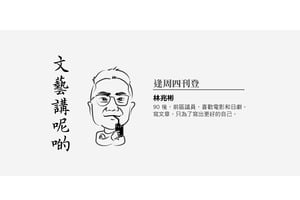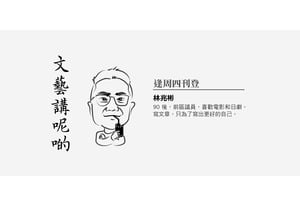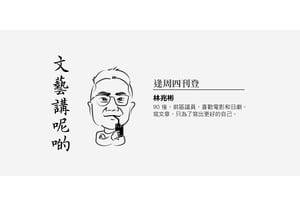最近看了由學者馬寶康(Malte Philipp Kaeding)於2020年推出的紀錄片《香港本色》(Black Bauhinia)。影片試圖呈現「香港本土主義」的誕生與發展,從本土民主前線的崛起,到2016年梁天琦參選立法會、再到運動者流亡的故事,拼湊出一幅本土抗爭的圖像。對於不熟悉香港政治的人而言,這部片確實具有導覽作用;然而,若將它視為對「本土運動」的全面紀錄,便會發現其敘事過於單一化,甚至帶有「神化」特定派別的傾向。
該片最大問題是將鏡頭過度聚焦於本民前領袖人物,如梁天琦、黃台仰。大量呈現他們參與街頭衝突、接受訪談、甚至考慮流亡海外的孤獨與掙扎,讓觀眾感受到他們的犧牲與勇氣。這種處理方式,雖能營造戲劇張力,卻同時製造了一種「英雄敘事」:彷彿本民前就是本土主義的全部,是唯一代表香港青年抵抗命運的群體。
然而,歷史的真相往往比影片所呈現的更為複雜。本民前雖在2016年一度聲勢浩大,但他們從來不是本土運動的全部。他們的瓦解也反映了路線選擇的侷限性。若紀錄片僅僅停留在「他們很勇敢、很悲壯」,卻未能深入探討為何這條路線最終難以持續,那麼觀眾所得到的便只是一種浪漫化的印象,而非對歷史的真正理解。
紀錄片當然不必做到「中立」或「客觀」;但若影像過度神化某一群體,忽略當年的外部批評,那麼它便失去了紀錄片應有的批判性。
「本土」不止一種,例如朱凱廸的「本土」路線在片中完全被忽略。影片若能將朱凱廸的故事納入,觀眾便能看見「本土」不是單一的激進抗爭,而是一個多元光譜:有衝撞體制的年輕人,也有在田野裏守護家園的村民與議員。遺憾的是,《香港本色》選擇以激進抗爭作為唯一視角,等於將「本土」窄化為「本民前式的本土」。
梁天琦無疑是《香港本色》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從2016年新界東補選開始,一躍成為香港政治的焦點,之後更因「魚蛋革命」被捕,成為「抗爭青年」的象徵。影片大量記錄了他的選舉現場、演說、與群眾互動,營造出一種「英雄誕生—英雄受難」的敘事。
然而,影片卻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背景:梁天琦其實是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那麼,為何他會成為最激進的「本土派」領袖?這背後的身份轉化與認同矛盾,正是理解香港「本土」的關鍵。
如果影片能深入探討這一層,觀眾會發現:所謂「香港本土」並非單純的血統、出生地問題,而是一種基於生活經驗、價值選擇的身份建構。梁天琦的故事原本能挑戰「本土=排外」的刻板印象,卻因影片的忽略而淪為單純的「烈士形象」。
《香港本色》所呈現的「本土」歷史,是一個被簡化的版本,但不可否認,它是一部有感染力的作品,讓觀眾能直觀感受到香港青年在抗爭中的激情與代價。對國際觀眾而言,它提供了一扇理解香港運動的窗口;對香港觀眾而言,它也是一段歷史的見證。◇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