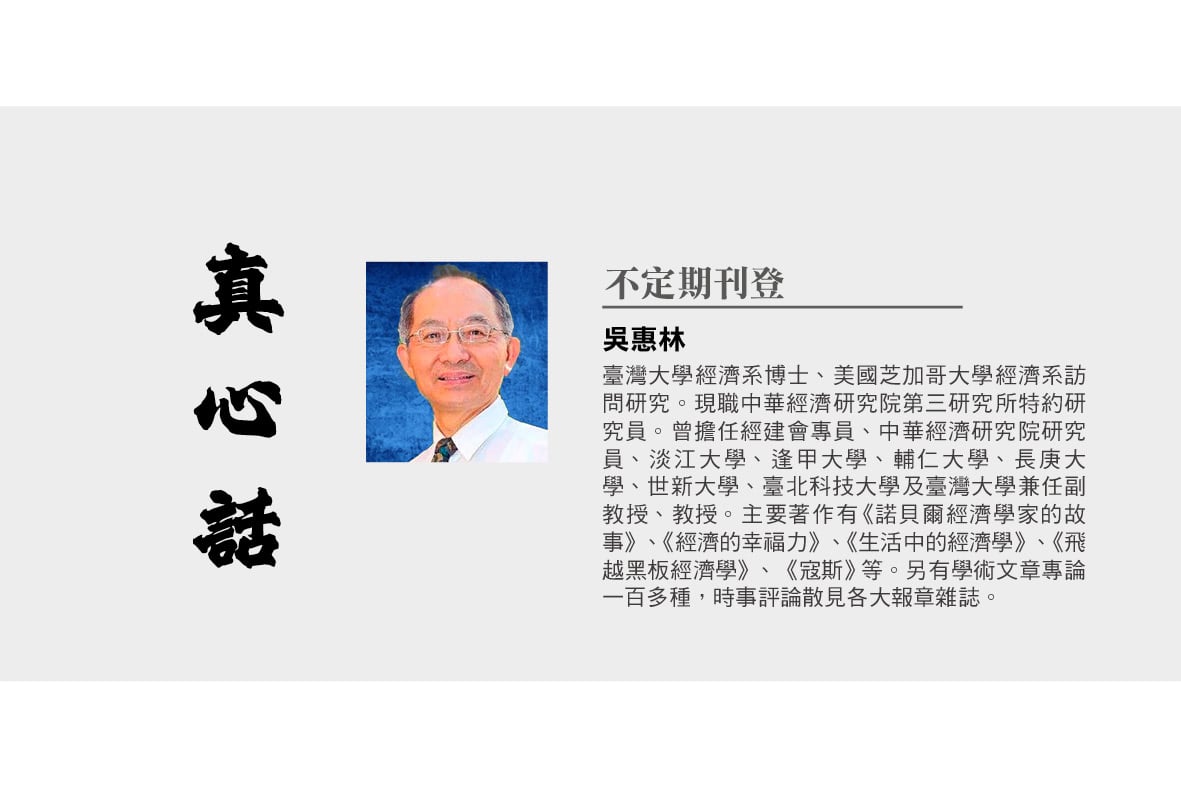2007年底的某一天,看完本書中譯本初稿,發覺很難下筆寫導讀或序文,因為作者自己已明白地在書中以<前言>和<導論>,以及在<結語>中全包了。或許我只能寫「讀後感」。
的確,誠如作者大衛・瓦爾許所說的,這是一本故事書,主角是一個人,以及他的一篇學術文章。不過,更廣泛地說,作者其實藉由這個主角和這篇論文講述當代經濟學的發展和演化的故事,時間涵蓋兩百多年,著重的是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重點在「經濟增長」、「知識」、「科技」這些名詞及其內涵的變化,而且引申出「政府政策」的角色該如何扮演,其終極目標還是在於如何促進全人類的「福祉」。其間涉及地區間、國家間、行業間,以及職業間的諸類結構性演變,可說異常龐雜。
困難度極高的工作
這麼複雜的事務,以四百多頁堪稱厚重篇幅要將之說清,執筆者仍然不但要有經濟學專業的基本功,還要有說故事的本領,而文筆要好當然更不在話下。那麼,要問的是,本書作者有此能耐嗎?
作者自稱是位經濟記者,且在報社工作多年,如此,文筆和說故事的本事想必沒問題;而在本書<結語>的前頭,作者明示他即將加入經濟學界,等於告訴讀者他擁有經濟學的底子。讀完全書,我也同意作者的確具備寫這麼一個難度相當高主題的三大要件,而本書的出版其實就是最好的明證!
此時我的腦中也再度浮現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Buchanan),他在《自由經濟的魅力·明日資本主義》(Tomorrow, Capitalism)這本書的英譯版序文中,對原作者李甫基(Henri Lepage)這位法國記者的讚詞。他說李甫基這樣一位經濟記者,「既具備冷靜精深的經濟學知識與合乎邏輯的政治哲學知識,又具有表達這些知識給廣大讀者的能力」。本書作者也同樣夠資格獲得這樣的稱讚。
李甫基在該書中寫的是「自由經濟學」再領風騷的精彩故事。這本書則主要記敘「知識經濟學」或「新成長理論」的發展故事,甚至擴及一般性的「財富」或經濟增長理論的演化,較諸李甫基,格局更大,難度更高。而且,本書還涉及經濟理論流派、經濟學數理化演變和經濟學教科書出現、蓬勃演化等等,工程實在鉅大。
這本書的主角名叫保羅·羅默 (Paul Romer),他的論文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刊在著名的主流經濟學術期刊《政治經濟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篇名叫〈內生的科技變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這篇文章是「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分水嶺,產生了一種革命性的變革。在此,有必要先扼要陳述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歷史沿革。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沿革
大致上,自從哈羅德-多瑪 (Harrod-Domar) 以「投資雙重性」為基礎,得出有名的「哈羅德-多瑪成長模型」之後,許多國家的經濟計劃即以該模型為藍本作推估,但因其具「剃刀邊緣」的不穩定特性,一旦離開均衡,即難回到充份就業的成長均衡。為了改進此種不穩定性,學者們乃分頭進行研究,其中,最成功者乃推梭羅(R. M. Solow,一九八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在一九五六年發表了<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項貢獻>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這篇重要論文。他將生產函數型態由梁鐵夫 (Wassily Leontief, 一九〇六〜一九九九, 一九七三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為資本、勞動之間可以任意替代的生產函數,以獲致充份就業的穩定均衡成長,從而「新古典生產函數」即廣為學界所引用。
梭羅的「新古典成長模型」有三個基本的假定:一為人口成長係外在因素決定的,經濟與人口變動之間沒有交互影響;二為生產函數呈現固定規模報酬;三為投資等於儲蓄,前者為資本存量的增加額,後者則為總產出的某一固定比例。就在這三個假定下,梭羅推導得出:某一經濟社會能夠達到,在某一資本勞動比例之下的長期靜止不動之每人所得,此時,社會呈現充份就業,所得增加率等於人口增加率,也等於資本增長率。
這個精緻的新古典成長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常與實際現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個靜止不動的長期穩定均衡方面,與我們熟知的,許多國家有連續成長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實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長模型推論出,技術與偏好相同的國家,每人所得會逐漸接近;這與世界銀行一九八四年的研究和顧志耐(S. Kuznets, 一九〇一〜一九八五,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 之研究都有違逆,事實上,貧富國家之間的成長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關於第一點缺失,梭羅加進「外生的」技術變動來解釋,他將技術進步視為「餘數」,因而得到有名的「技術進步梭羅會計估計法」。迄今,這種測量法仍廣為台灣學者所用。但因此法需要用到難以得到公認的資本存量資料,而有其它測量法的出現。其中,已故的邢慕寰院士也曾自創一種不用資本的估計方法,但仍有爭論,有待進一步研究。
沉寂十年再抬頭的成長理論
由於新古典成長理論存有重大缺陷,到一九七〇迄八〇年代初期,就不獲經濟學家青睞。但是,就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情況卻有變化,數位當代頂尖的學者,不約而同地將它重提,並再改造成理論。最值得注意者當推盧卡斯 (R. E. Lucas, 一九九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和貝克 (G. S. Becker, 一九九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兩位教授。兩者都針對上述梭羅成長模型所無法解釋的「富國、窮國之間,無論在個人所得的絕對值或增長率上均有所差異」,試圖提出新的解釋方式。
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資本的加入找出一個模型——個可以放在電腦裏跑的明顯動態體系——以機械化的運作架構來反映此等事實。後者則再引進馬爾薩斯 (T. Malthus, 一七六六~一八三四)的經濟動態模型,將人口成長視為內生變數,結合梭羅的模型,重新再出發。迄一九八〇年代末,兩人皆各有可觀的進展。他們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別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和一九八七年三月到台灣訪問時,作過公開演講。
經濟增長理論在沉寂十多年之後,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再重現曙光,而一九八七年梭羅這位現代成長理論先驅者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成長理論又再度重領學術風騷的證明。不過,此時真正的主角既非梭羅,也不是貝克或盧卡斯,而是羅默。
知識經濟學崛起
羅默可說出身自芝加哥大學經濟研究所,也受過盧卡斯的薰陶,但他的理論與芝加哥學派卻有杆格,特別在「政府干預」這個關鍵點上,這點也是所謂的「淡水學派」(主張政府不應干預)和「鹽水學派」(主張干預)最主要的差異。自一九三〇年代凱因斯理論興起,從此以後「政府精密調節經濟」就廣受歡迎並被認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所得政策、產業政策等紛紛出籠。
「市場失靈」的理論是政府能堂而皇之進行干預之基礎,尤其是所謂的「Public Goods」(一般書本都稱為「公共財」,其實是錯誤的譯法,而英文名字也非常地不妥,因為這種種財貨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兩種特性,但「公共」或「Public」的意義卻是大家共有的物品,與「私有」相對應,這是「產權」的課題。而且不論是私有財或公有財,都可能有著共享和不能排他兩種特性。不過,大家不妨想一想,實際社會裏真有同時擁有這兩種特色的物品嗎?即使是「國防」,也可能利用驅逐出境予以排除呢!因而嚴格地說只能找到「近似」具此兩種特質的財貨而已),更被認為應由政府免費提供,因其一旦製造出來,廣大的其他使用者就不必支付成本而享用,且不會減損他人的好處。(對此重要觀念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吳惠林(二〇〇五),《飛越黑板經濟學》第二篇《市場失靈的迷思》,頁一四七〜 一七二。)
羅默的「內生技術」之理論基礎就是「知識具共享性」。對於人力和科技資源所發揮出的創意、創新,必須有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於是原本似乎永遠也無法與央行總裁、財政部長,甚至貿易談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學部門主管與教育部長,由於科技、訓練,以及教育政策將被全世界所有國家視為政府必要與合法的責任,其重要性與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參加執行這些政策的難度甚至更高,所以這兩個部會首長的地位乃水漲船高,特別在知識經濟興起,電腦科技日新月異,互聯網無遠弗屆的二十一世紀,將更為明顯。
稀少性和生產要素產生破天荒變革
在經濟理論上,「內生技術變革」所表達的是「報酬遞增」或「生產力向上」的情況,而襲斷性競爭市場也取代完全競爭市場,於是「稀少性」這種經濟學一直以來的假設將被「富足性」取代,而過去二百多年來經濟分析的土地、資本、勞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東西」取而代之。為了明確表明此種變革,就必須以高深數理模式來呈現,經濟學數理化的境界乃更見提升。 我們知道,經濟學之所以在一九六八年被瑞典中央銀行出資列在每年頒發的「諾貝爾獎」行列,係因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數理化」程度最深,且可用計量方法來實證。這條數理化之路始自馬夏爾(Marshal, 一八四二〜一九二四),迄至 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 一九七〇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才備妥工具而發揚光大,他用新方式寫作之《經濟學》暢銷書更將此工具發揮得淋漓盡致,而經濟體系可用數理模式表明,政府可用政策「精密調節」(fine-turning) 經濟景氣,乃至提高經濟增長,開發中國家和落後國家也可依樣畫葫蘆,或許貧富間差異得以縮小,貧窮得以消除,乃至世界大同可以達成!
瓦爾許的這本巨著就是講述成長理論和經濟學演化的故事,他以記者的寫作功力很精彩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俗話說「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無論是經濟學圈內人或門外漢,都可以受益。誠如作者所言,一些讀者可能偏好跳過這本書的背景部份,直接閱讀各種指南或剛剛開始出現的教科書,但這將因此種倉促而錯過一個好故事。或者讀者們先看過我這篇讀後感和本書的前言、導論和結語後,就會有一窺全書的興趣。
返還亞當·史密斯的世界
這本書不但精彩講述當代經濟學的演進,作者更點出了重要的意涵。不過,正如作者在本書最後一段所指出的「經濟學讓人興奮的盛況目前已達顚峰。不過最大的挑戰仍然橫亙面前,比國家財富更「深層」的秘密還有待發現,也就是亞當,史密斯稱之為道德情操的天賦—關於人性,也是我們宣稱的人道。」畢竟羅默所帶動的新成長理論或知識經濟學,係基於高科技的帶動,而由創新的日新月異讓報酬似乎遞增,人類也好似越來越富足。可是,不說全球「赤貧」還消除不了,連先進國家中都出現明顯M型社會,中產所得階層流向低層者眾,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動連綿不絕且越來越恐怖,恐怕都是可怕的後遺症。
人啊!何不勇敢承認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財貨之富足卻以摧毀無形的心靈作為代價,又讓地球資源快速耗竭。
那麼,不是如本書作者所說的,應該是到了喚回當代經濟學的始祖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感)」或「倫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時候了嗎?#
※二〇二五年諾貝爾獎頒給三位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經濟學家,顯示經濟增長再受關注,科技、創新是主角,而十七年前出版的這本書,更顯出一讀的價值。
(本文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