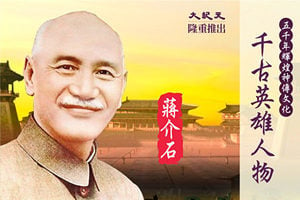又是政治課的時間。同學們心不在焉地坐在教室裏,有的看著窗外,不知在想著甚麼,有的做小動作(上海話,即不專心上課做自己的事情),有的女同學則在桌下織毛線……
班主任兼政治老師「橫長」(同學給的綽號,肥肉橫向長之意),同往常一樣,從口袋裏掏出「毛主席語錄」,大家也自動地翻開自己的毛語錄第一頁的由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所撰寫的「再版前言」,唸了起來:「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就在這時,所有教室裏的擴音器一起傳出了一陣刺耳的迴旋聲,打斷了大家有氣無力的聲音,擴音器裏隨即傳來校長濃重的江北口音:「老師和同學們注意,現在我中斷所有課程,來傳達(中共)中央下達全國人民的緊急文件。」「⋯⋯林彪等人策動武裝政變陰謀敗露,乘飛機出逃後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墜機身亡⋯⋯」這突如其來的驚人消息,震醒了全班近六十人,大家都鴉雀無聲,聽著校長繼續說他那滑稽的江北口音—上海腔—普通話,腦海中都浮現一個問題:為甚麼已被偉大領袖確定為接班人的人,會策動武裝政變,要想推翻偉大領袖呢。這也是當時所有的人開始思考卻始終想不通的問題。
「接班人」政變失敗後,「四人幫」成為了貫徹文革思想的主要推手。復出不久的鄧小平則以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為目標,在各地重新啟用了老幹部掌管領導權。但他在鬥爭中失勢,再次被免去所有的職務。「四人幫」因無法奪取軍權,就利用上海這個他們多年苦心經營的重要據點,組織民兵,建設「第二武裝」。企圖以上海民兵發動武裝叛亂。
為了執行市革命委員會「訓練」要求,學校在學期中各三個月的「學工」「學農」之外,又加入兩個星期的「拉鍊」,即背著自己的棉被等背包,沿海岸線每天走上三四十里的路,晚上在人民公社提供的的簡陋屋子內過夜。睡在那僵硬、高低不平的泥土地上,腰酸背疼地難以入眠。清晨,人民公社農田地中的大喇叭響起了「東方紅」歌聲,我們頂著寒冷的海風中步行去村中的水井,打出冰冷的水洗潔。由於柴火不足,學生們自己做的伙食都是半生不熟的「夾生飯」每天都是一樣的椰菜,沒有任何有營養或入味可言。一個要好同學的媽媽給他做了一瓶辣豆瓣醬帶著(當然也增加了自己背包的份量,造成了行走的負擔)。他會分給我一些,加拌在夾生飯中下嚥。我們的腳底磨出了大小的水泡,水泡破裂後,疼痛無比,又沒有包紮。第二天繼續行走在崎嶇不平的路上,疼痛得難以忍受。
在混亂中的「復課鬧革命」的號召下,由於我在家自學過數理化自學叢書,在學校教的那些代數、幾何等課程都是全班第一。對我的成績,「橫長」非但不予獎勵,反說是「白專」,沒有做到在政治表現出色的「又紅又專」。學校的英語課本也不見日常用語,而是:永遠不忘階級鬥爭、馬列主義、毛思想等等。
我爸爸是一名主任醫生。因為知識份子的個性,不相信外行的黨幹部領導內行,得罪了領導,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帽子,遣送去山東省邊緣偏僻鄉村一個小醫院工作。媽媽原在上海醫學院任教,也下放到浙江省金華地區的農村。她帶著年幼的我,離開了上海去金華當「赤腳醫生」,即農村的流動醫生。金華地區貧窮,沒有農業機械化,農民們光著腳在稻田裏插秧,造成血吸蟲病大流行。災難給人民帶來了極度的痛苦和物資缺乏。雖然政府發放的糧票、油票、肉票等二十多種的各類配給物資票證,老百姓也還是買不到足夠的基本食物。一次回上海探望外婆時,外婆給我做了一個荷包蛋。我好奇地問道:奇怪,上海的荷包蛋怎麼是圓的?外婆說,難道金華的不是嗎?我說不一樣,金華的荷包蛋是三角形的。外婆聽了不出聲。她明白,那是因為沒有足夠的雞蛋供應,只得把一個蛋切成兩半分開來吃。在探親假期結束後回金華的那一天,我哭著懇求不要再去那個地方。但是一切都是無法改變的了。從家門口到去火車站的15路公車車站的路上,鄰居、行人都同情地問這個小孩子為甚麼如此的悲傷……就這樣地到了火車站,上了火車,直到金華時已哭乾了眼淚。
金華是著名的金華火腿產地。為了賺取外匯,火腿一律只外銷海外或港澳地區。本地老百姓則無法購買。一天單位裏組織開會,說是落實黨的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幹部要求我媽媽在會議上給政府上提出一些批評或建議以便政府能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我媽媽膽小怕事,推說一切都很好,沒有甚麼可說的。但在領導的一再壓力下,她就說,金華的食品店裏都掛著火腿展示,但老百姓卻買不到,吃不著。誰知這下可中了計,不得了。在幾周後的會議上,被點名批判,罪名是惡意誹謗政府。這種「罪行」本當足以被扣上「黑五類」之一「右派分子」的帽子。據說當時因為考慮到她的姐、弟在海外,這樣做不利於政府當時對海外華僑的統戰工作,因此暫時沒有將她列為「右派分子」。
我媽媽好不容易地從金華調回上海(始終沒有嚐到一屑金華火腿),安排在一個區級醫院工作。但夫妻分居兩地,爸爸每年只有一次回上海探親徦的機會。每次回山東他都會帶大包小包的糧食,由我放在單車上,騎去火車站給他帶回山東貧窮的鄉下。上海北站的候車室裏總是擠滿了熙熙攘嚷的旅客及家人,大家都是帶著大包小包的物資去全國各地。雖然火車票都有定座位,但因行李過多,旅客們搶佔行李架成了非常辛苦的事情。每當車廂的門一開,大批人肩上抗著、手上提著大包小包一個勁地往車廂裏擠,將車門堵得水洩不通。每次我都要爸爸先一個人擠進車廂,然後打開車窗,由我從車窗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遞給他。火車慢慢地啟動離開月台,我不停地向他揮手,真希望他可以在家裏多住一些時間⋯⋯。
在他即將返回山東的前一天,是一個溫暖、美麗的秋天。全家一起去長風公園遊玩。長風公園是上海附近最大的公園。園名來自《宋書‧宋愨傳》中的「願乘長風破萬里浪」之句。園內浩瀚的「銀鋤湖」畔,岸柳成行,湖中碧波清晰得能照見人的倒影,後面的「鐵臂山」影在煙波中隱隱綽綽,猶如世外桃源。我們中午從餐廳裏用配給的糧票買了木板片餐盒什錦炒麵,在和暢微風中的綠州湖畔野餐。真是淡飯粗茶分外香。爸爸用黑白120膠卷的相機,在夕陽下記錄了我年少時最快樂的一天。
在媽媽工作單位裏,每周二和周五,無論多忙,多累,下班後都必須加兩三小時的政治學習會。會議後已經是晚上八九點鐘。和同事去街上吃一碗熱騰騰的鹹菜肉絲麵,那情景成為了她一生難忘的回憶。在一次晚上政治會中,領導要求員工加入極左的「工人造反隊」,或是支持老一輩黨幹部組織的派系。媽媽由於海外關係,屬於不可信任群體,沒有被要求加入隊伍,但領導還是要她表態支持哪一派。因為有了上次「金華火腿」的教訓,她說支持「造反隊」吧。心想「寧左勿右」不會有錯。誰知此舉又鑄成大錯。那個院長,一個黨的老幹部,在四人幫倒台以後,重新掌大權。把所有參加過「造反隊」的職工,一個不留地發配(撤銷上海戶口)去雲南省邊遠地區。至於我媽媽,在以後的十幾年裏,沒有加過一次工資,不給任何陞遷的機會。並想方設法地阻擋我爸爸在政治上平反後重返上海工作的申請。
在經歷了這麼多的苦難之後,我媽媽都從來沒有對我談起自己是否後悔在解放初期的時候由香港返回大陸,她只是常說共產黨的組織和統戰能力厲害得很。她和兩個姐姐跟著父母,全家在上海淪陷(解放)前夕逃離去了香港。外公是一個工程師,任上海某研究所的所長。大陸解放後,特別需要專業人才維持各階層單位正常運行。媽媽在上海一個最好的朋友同她通訊聯絡,說新政權是一個清廉、真正為人民辦事的政府。勸媽媽和她父母一起回祖國。與此同時,外公的研究所的幾個部下也寫信給他,請他回去繼續當所長,並說保證如同以前一樣的待遇。當時他也懷念家鄉和研究所的事業。就這樣,我媽媽和父母又一起回到了上海(還好她的兩位姐姐決定留在香港)。回到上海後,我媽媽激動地去找那個最要好的朋友,卻無法再找到她了。後來才知道她已調去北京當了某個局幹部,我媽媽這才醒悟過來,原來這位最要好的朋友是一個地下黨員,完成任務後就離開。另外,那幾位曾經勸說過她父親回國的前部下也都一起突然消失了⋯⋯。
我們學校門口的灰色水泥牆上貼滿了「聽從黨的號召,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等的標語,為我們的「畢業分配」作宣傳造勢。由學校決定每個學生的前途,或分配到本市工作單位,或是參軍,最優惠的待遇,只有三代工農兵家庭出生的才有資格,退伍後均可分配到好的本市工作單位。同樣優惠就是進大學深造。最差的就是到邊遠的農村「插隊落戶」。一切都根據學生家庭的出生背景、家中哥姐的的工作情況由學校決定。一個鄰居家的同屆畢業生,三代工人階級,不僅曾被分配到重點學校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學習,這次畢業分配中,也安排進入海運學院深造。在他被學院編入後,學校組織隊伍打著紅旗來他家為他慶祝。那一天,在鑼鼓聲中,穿著一身嶄新的學院白色制服的他,笑容滿面。英姿勃勃,興高采烈的樣子,我在隔壁樓上的窗口看見,無比羨慕。也為自己前途感到悲傷。「橫長」為了立功,來家裏動員我下鄉。每幾天就來家中一次,施加壓力。我就是不去。
隨著「偉大領袖」的過世和四人幫的垮台,那場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永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形式上似乎已成過去,但它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破壞,也繼續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數年後,我終於踏上了自由旅程。在走過了最後一面高掛的紅旗,沿著「往香港」路標指示牌走上了羅湖橋。橋面中間有一白色線條,標誌著中英邊界。橋的另一端有一面旗幟在新界的春風中緩緩地飄揚。那是一面深藍色、白和紅色組成的「米字旗!」我當時興奮的心砰砰地都要跳了出來。情不自禁地加快了激動的腳步,提著沉重的行李,急速越過了那條中線,踏出在自由道路上的第一步。
羅湖至九龍的火車站上,看到每一個人身著不同顏色、款式的服裝。同我熟悉的的藍、灰色單調的中山裝、兩用衫,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火車車廂內,一群和我年齡相仿的學生們在郊遊返家的途中,他們歡樂交談的笑容,是如此的真摯和自然。這是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笑容。一瞬間,我突然明白:這就是自由!是自由空氣裏才有的燦爛笑容⋯⋯。
在紅旗下成長的我們,都有自己辛酸的經歷和故事。無論今日在何方,或者你選擇沉默,或把它們忘記,但它們在你的記憶中是永遠無法抹去的。#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