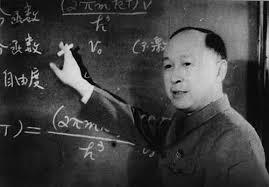【大紀元訊】(接上文)
我媽差點自殺
1967年夏天,集中營被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管,又關進來一批八大院校的「反動學術權威」,都是教授、博導、有名的院士,頂級專家,不少人是從國外回來的。集中營改名叫「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人們說的「關牛棚」,每天組織這些「牛鬼蛇神」學習,在毛主席像前「早請示,晚匯報」。
早上起床頭一件事,要求我們面對面兩排坐在鋪上,背毛主席語錄,每天背的頭一條都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必須一邊背,一邊指著對面那個人,他指著我,我指著他,互相指著罵對方「反動的東西」。
漸漸地,有人被送去勞改,其他人被發配回原系統監督勞動。我被分到交通部下邊一個工廠,一周放一天假可以回家了。經過這個漫長的冬天,我第一次見到了我母親。
我後來聽說我媽當時都想自殺,跳紫竹院那個河去,她把衣服甚麼的都準備好了。我弟弟好歹勸住了她。她想:唉,都是因為我嫁給了一個「混蛋」,把這孩子弄成這樣……她一個太柔弱的女子,帶倆孩子,沒有任何靠山,你讓她怎麼活?
受教於科學家華羅庚、錢學森
我們這批黑五類,當時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比在外邊挨鬥、受衝擊的人更慘。我在那裏邊是最小的,現在都70多了,絕大部份人可能都不在世了。由於很長時間沒有說話的權利,等人再出去,已經說不了話了。而且受過這種刺激,相當長時間根本不敢思考。
我能活著出來,就感覺:唉,到底能讓活了啊!現在我怎麼活呀?下一步我怎麼活著?
每個星期天一早我就出去轉悠,去這麼幾個地方:虎坊橋、前門的中國書店,那年頭新華書店沒有書,但是你去中國書店,抄家扔的各種各樣的書、專業書太多了,而且極便宜。還去王府井外文書店,它在金魚胡同,原來外文出版社內部的一個小樓上,上那兒找一些國外有關裝備方面的書。別人搞階級鬥爭去了,我想把專業和外語拾起來。
有一天,我在東單公園裏溜躂,看見一個老頭,在那椅子上坐著,眯縫著眼睛。哎,這不是華羅庚嗎?我見過他照片,大學畢業時在人民大會堂聽過他做報告。他是中科院數學所的研究員,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那時也靠邊兒站了,正憋著沒事兒呢。
我就過去跟他搭訕。他一看,一個小孩兒。聊幾句,知道是個大學生。我是學應用物理的,但裏邊有些數學的邏輯問題,我就請教大師。那個年代,沒人跟他講話,突然有人跟他討論科學,他高興死了,那意思「我可碰上你了!」
他住在崇文門,離東單公園很近。從那以後,我遇到科學上的問題,經常跑去向他請教,我們成了忘年交。這是文革中比較快樂的一件事。
大師嘴裏聊出的東西,跟學校老師照本宣課教的很不一樣。大師講的是他腦子裏成天琢磨的事,一定是精華,很自然地聊出來。我知道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那些年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鼓勵著我在苦難中活下去。
純粹出於對自由探求思想的熱愛,出於追求智慧的天性,想聽聽大師們是怎麼看這個世界的,我自己又設計了去找錢學森。我知道他住在永明路那個大門裏頭。我就坐巴士去踩點,費了不少勁偵察。他家對面有個賣主食的小飯鋪,邊上有個菜站。他下班都是一輛伏爾加送他回來,我不能過去攔著他,那太唐突了,於是就買個炒餅,來碗餛飩,坐那兒花半天時間等候,邊想著自己的事。
那天,他下車後上菜站買了點菜,我就走過去畢恭畢敬向他鞠了一躬。錢先生說:「哦,你認識我呀?」這時他身後的大門打開了,他夫人蔣英開門問:「哎,你怎麼還不回家呀?」我一聽,壞了。沒想到,錢先生說:「你把菜拿回去吧,這裏有個年輕人願意跟我聊兩句。」我一看有戲,樂壞了!
我請他在邊上的小飯鋪坐一坐,從他發表的某些文章開頭,向他請教力學方面的基礎問題。
他講的非常深,當時我沒太聽懂,後來才慢慢悟懂的。那次之後,我又跟他交談過五六次,都是我在那兒等著他,有時也等不著,碰巧他正好有功夫的時候,他會說:「啊,小伙子你又來啦。」我倆就還在那個小飯鋪裏坐著聊會兒。這有點像帶研究生、博士生,互聊互動的思想課,挺有意思。
跟錢學森接觸後,才懂得了自動控制系統工程方面的思考,屬於系統論,比清華學的深得多。一切按照系統的概念整理思想,才能做得有序,實現起來就是系統工程。
我不是大師,但這個階段打下的基礎,使我很多年後再碰到那些中科院院士,可以橫掃,跟他們進行思想對話。
燒煅工爐
我們那個廠是亞洲最大的汽車修理廠,我作為監督改造對象,前前後後在那兒待了11年。
剛去時分配我修理汽車。過了一年,廠裏突然作出決定,你這反動分子不能幹技術活,得去幹粗活,就把我調到煅工車間,做鈑金煅工。我學著打了兩天鐵,又說,這也是技術活,你不能幹,你去燒煅工爐吧。
煅工車間的爐子比燒煤的火車爐子要大得多,有一個大撬門,大概38斤重。從煤堆到爐前大約70米,下料的小推車裝一車煤是半噸,每天我得把48車煤,也就是24噸,從70米外推到爐前,再通過小爐口,把煤全部扔進去,爐子內長11米,你得扔那麼遠。每天七八個小時,不斷給爐子加熱,得保持爐溫老在1100度左右。
清爐,一般一個人幹不了。爐子會結渣,結成瘤子似的,粘在大爐子底下的通風鐵條上。得把它們撬起來,再用大耙子耙出來,晾涼了之後送到廢料場。必須一天一清,原來三個人弄個大鐵槓,才能清得動。
過去三個人的活,現在讓我一個人完全憑體力完成,而且沒有任何防護措施。新來的退役軍人說:「他們真欺負人嘿。」
下了班,別人可以走了,我還得去改造班,跟廠裏的黑五類一起接著幹。去工廠的大煤庫撮煤,挪到另一邊去。有個資本家說:「小李,你那麼賣力氣幹甚麼?你挪到那邊去,你看著,待會他還會讓你挪回來。他不是真需要,他成心折騰你呢。」
我下班都晚上七八點了,早上還要趕在八點鐘上班,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廠裏有班車,我早上坐過兩次班車,讓車間主任把我轟下去了。他說「你下去!」那意思,你是反革命,不能坐這車。我就下去了。從此,我每天早上五點就起來坐頭班車,途中要倒三趟車,還得走很長的路。
我像個木偶似的 到處當靶子讓人批鬥
整個文革是一個大的時期,中間還分成很多小的階段: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抓5.16、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
每次運動來了,都要把我翻出來再揭批一通,跑不了。還要千方百計找出我有甚麼新的現行反革命行為。我被看管起來,不能回家。
有個書記特別壞,他讓我把日記交出來。我覺得我日記裏沒寫甚麼,無非是日常在哪兒買了甚麼書之類的,你就拿去看吧。結果就變成了反動日記,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證。
比如我日記裏寫道,我站在學校的樓頂上,站在西山,看北京城,北京城就像一個火柴盒。他們就說:北京是革命聖地,世界革命的中心,你把它說成火柴盒!
我日記裏還有這麼一句:「這裏在播種仇恨。」我忘了自己寫過這句話,結果讓他們揪住了,這又是反動本質的大暴露。
每個星期有兩次固定的全廠批鬥大會,站在台上挨鬥的準有我。身後兩個工人把我撅起來,人們在台下高喊:「打倒李XX!」
剛開始,我差點就受不了了。我在的煅工車間有個游泳池,當時我真想……真不想活了。
沒人跟我這個反動分子說話,常常整個一天,一句話都沒有。誰都不拿正眼看你。打飯的時候,跟師傅說要哪個菜,他給你盛菜那個表情就跟打發狗似的。也許有人心裏有點同情,但他不敢表露。
我作為典型標杆,還要巡迴到各小組挨批鬥,這班批完上那班,一天兩三個地方。後來我就疲了。那麼大一個廠子,我就像個木偶似的,到處站那兒當靶子,讓他們批。十幾個人的小組,喊幾句「打倒李XX!李XX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就讓我走了,到哪都這一套。我面無表情,木呆呆的。有表情更麻煩,當時就會問你:為甚麼笑(哭)?新的批判詞又出來了,會延長批鬥時間。
他們批鬥我時,我沒聽見,在想我自己的事。我已經成熟了,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生存技巧。日記也根本不寫了,對歧視也已習以為常。讓我回家就在家想事,不讓回家就在單位想。主要是在自然科學裏積累,探索一直沒停。允許休息就轉一轉,找哪個專家,談談這段時間的思考,再學習他們的思維方法,看看師傅領的路上我有甚麼偏差,有新的問題問一問。
逐漸地,我形成了自己的活法:有功夫就學本事,有時也探索人生觀問題,在舊書店找些書看,像西方哲學家羅素的書,佛學的大乘小乘,小說之類。我沒有深陷痛苦,也不刻意逃避,寵辱不驚,順著天命的安排,完成我這輩子完善自己的過程,走我自己的路。後來我看到幾本佛教故事,覺得是很高的境界,很合我當時的心境。
在工廠的十一年,就是這麼熬過來的。對宇宙萬物關係的思考,對人生的思考,在若干年後最終把我引入了天主教。
「毀我長城一塊磚」
有一批當兵的來我們廠實習。我去幹活時,把手錶放在更衣櫃裏,那時更衣櫃都不上鎖。下班回來發現手錶沒了,我說了出來。起初那些當兵的沒敢走,後來領導說,「解放軍同志先走吧。」又在工人中查了半天,沒結果,最後指著我說:「你是不是就為了毀我長城啊?」那意思,早不丟晚不丟,解放軍在這你丟手錶,是想拉黑、污衊解放軍。
又開了我一個批判會,大字報也出來了:「李北海反革命本性不改,毀我長城一塊磚。」我辯解:手錶確確實實丟了,我也許不該說,但我根本沒說解放軍,絕對沒有攻擊解放軍的意思。以後也就不敢再提,新買了一塊手錶完事。
結果還真是那塊磚有問題。轉過年,書記找我說,你那個表給你還回來了,就是解放軍裏一個人偷的。原來那批小兵快退役時,他才敢把那塊表戴出來,讓另一個小兵看出來,給報告了。書記說,你就不要聲張了,不然你這不是臭解放軍嗎?
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怎麼把人性變壞的?
每次運動來了,先開動員大會,敲打說:階級鬥爭動向我們已經有所洞察,掌握了一些情況,你自己掂量著點兒,革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台下每個人心裏都得嘀咕:這是不是說我呢?我平常是不是有這種表現啊?然後就互相算計上了:我們之間說過甚麼,我如果不把他說出來,他該把我說出來了,我趕緊先把他說出來吧。
每輪運動都有指標,上邊還會來摻沙子,做工作。比方說,一個單位一定要抓出兩個典型來。人們心裏就想:反正別是我,趕緊弄出倆來,我就安全了。有的人為了自保,有的人甚至想投機立功,就充份表演自己的革命性,從人群中找個替死鬼,踹你一腳:去死吧你!而我,恰好可以填充那個替死鬼位置。
經常有這樣的,平時他倆關係挺好,如果都能自保,誰也不會說誰,一旦有了危險,有人揭發咱倆了,就顧不了這麼多了。「哥倆好,哥們實在對不起了!」——是當時工人中的一句流行語。
尤其到文革後期,這種心理很普遍。人人都想自保,就人人互害,人與人的鬥爭變得非常殘酷,結果人人都不安全。就變成這麼一個社會了,人性就完了,很可怕。
再一次被打回地獄
1971年,9.13林彪事件爆發,毛澤東受到刺激,鄧小平復出。之後,整個大氣候有個變化,開始搞抓革命促生產,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繩子鬆動了一點。車間主任讓我給新蓋的煅工車間做個加熱系統,那個大車間的加熱系統全是我做的。又讓我把原來燒煤的爐子改成燒油的,能燒輕油又能燒重油,我也做出來了。批鬥的事少些了。
有了新爐子,我不用推煤了,也沒爐渣了,坐那看著爐子,調調爐溫,挺舒服。下班後也不用參加反動分子的改造了。還讓我參加了廠子的足球隊。我媽戲唱得好,從小就有名角調教過我練基本功,所以我又參加了廠子的文藝宣傳隊,還幫著編導舞蹈。大學時,我苦練過吹笛子,達到專業水平,廠子就叫我把樂隊組織起來,我還當上了樂隊指揮。
1972年12月21日,工廠在禮堂開大會宣布我「解放了」。
人們看我的眼光變了,之前沒人敢跟我說話,突然有人跟我說話了,他們好奇:這麼年輕一個反革命,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有人問我:「鬥你時你自己一個人在上面,大傢伙都看著你,害臊不害臊?」我說:「有甚麼害臊的,都是革命群眾,你們不是在搞革命鬥爭呢嗎?」
我從來不跟他們開玩笑,仍然夾著尾巴做人,保持低調。我心想,做的事要顯示出,從我這個家族出來的,從人性上、從各方面比一般人都強。我追求的是高格調、更高級的人生。
從1972年到1975年,太平了三年,又颳起了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再一次被打回地獄,作為典型上台挨批鬥:你看這反革命,現在還得了勢了,整天忙忙叨叨,跟個明星似的,人五人六的,他從根兒裏就反動,一輩子都是這個。
原來廠裏把我吸收進技術革新三結合小組,讓我設計汽車的二級減速。一個書記說,「他就是能設計出來沒齒輪的汽車,我們共產黨也不用他的。」共產黨永遠不會把我當自己人,我只是它改造監督利用的對象,永遠是敵人陣營的。
甚麼足球、宣傳隊、技術革新,一下子全停下來!重回煅工車間,讓我去打鐵。星期天別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得去弄花生。這種日子大概有半年多。
與戀愛、成家無緣
技校學生裏有幾個小姑娘,看我在那弄花生,這不是宣傳隊那個李師傅嗎?她們不參加工廠的運動,不知道我正在挨批鬥,就過來跟我聊天,往書包裏裝花生,覺得挺高興。書記過來了,走走走走!把她們轟走了。
1975年我已經三十出頭,說實話,根本沒產生過對異性的感情,也沒人敢跟我。有不知根不知底的人,偶爾提一句,我就當句笑話。我經常拿本聊齋翻看,覺得挺有意思。誰要給我介紹對象,我就說,你拿這個看看。意思是,你知道我是「狐狸精」的時候,你還敢找我嗎?
很早我就把戀愛、婚姻的可能性推到一邊,逼著自己連想都不想。我明白,跟別人有這種接觸,對別人就是災難。那時候,人的正常情感、願望完全被抑制了。
人心起了微妙的變化
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文革非常重要的節點,我漸漸看出來,大家都有點詼諧、調侃的意味在裏面了,那意思,你小子怎麼又來了?怎麼又是你呀?我從台上下來,感覺腳有點麻,在那兒緩緩,有幾個工人路過:「嚯,還活動活動啊!」氣氛輕鬆,沒有了那種虔誠、真把我當反動死敵看待了。
有幾個歲數跟我相仿的工人說,「你這命啊就這樣,共產黨到了啃節上準得把你弄出來,你小子是老運動員了。」
整個社會,包括統治體系內部,對文革普遍感到不滿,心灰意冷,已經不拿它當回事了。所有人都感覺,整個一個胡鬧!過去說,大饑荒是因為蘇聯逼債,農業欠收,大家都咬牙忍著,跟黨和國家一塊渡過難關吧。現在突然發現,毛澤東、共產黨一直在人為瞎折騰!根本沒個頭。前兩天還讓鄧小平復出,說變臉就變臉,今天說煤球是黑的,明天又說是白的,所有的說辭都是假的。既然都亂成這樣了,那就再亂一次吧,跟著演場鬧劇而已。
當初人們之間為了某種主義,能瞪眼,能分家,能離婚,現在就是一笑:我們那會太幼稚,太荒唐了,讓人家給耍了,騙了。
就說漲工資,連著漲了兩次,工人說的一句標準話就是:「您幾旗兒呀?噢,還是您的旗高,您先上。」指的是毛澤東思想紅旗舉的高不高,決定著你能不能漲工資。旗舉得不高,這回還沒您的事。完全是一種嘲諷。
我還記得,有一次軍代表給黨員講黨課,正面宣傳中共所謂的抗日史。他們下來在那議論:「鬧了半天共產黨就是一個慫尖尖,躲在後邊,淨是不光明正大的事。」
這都是天地間的,整個社會非常大的變化,人心變了。逐漸形成了一個全社會的覺醒反思,不再受某種組織的控制,人性和理性開始復甦。
1976年清明節:反抗爆發
1976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發生了很多重要的事: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連續死去,唐山大地震。四五運動並不是表面的悼念周恩來,也不是單純針對四人幫,是人們憋在心裏多年的東西,藉著四人幫這個出氣閥,一下子爆發出來。
那時候紀念碑還可以隨便上,到處都是花圈、輓聯、詩抄。周圍不知誰拉了好多鐵絲,鐵絲上掛滿了小字報、紙貼。膽子大的人寫出自己對政治的看法,有的很尖銳。
四·五我也去了天安門,跟著我們廠好幾百人去的。我看了看,沒有人組織,人們都是自發的,真是人心所向。我看到馬路對面,有文化藝術界的人在遊行,喊的口號很激烈,我認識的著名歌唱家也在隊伍裏。他們都比我大了十來歲,走在整個文化部隊伍的第一排。
工人糾察隊的棒子隊衝進廣場,打人、抓人——中共政府動用專政機器想滅掉人們的怒火。但是老百姓已經不太聽它的了,開始掙搏,反抗。雖然運動被鎮壓下去,很多中國人還不太敢想這個根源是毛澤東和共產黨造成的,但人們對階級鬥爭這套東西感到厭倦,事後的整肅已經發動不起來了。更多的人開始以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思維方式深入反思。
這個體系明顯走向窮途末路,毛澤東也明白,他建立的這一套已開始瓦解,玩不靈了。他預感到,自己也快要死了。
黨給我平反 我沒有任何感恩
「四·五」之後,我就不怎麼去工廠了。我反思了很多:共產黨這個統治集團控制整個社會的能力,不是一種自然力,而是一種抗自然的,完全喪失人性、反人類的勢力,就像把每個人的鎖骨都穿上一根鋼絲,強制拽著你。你們說這個國家是你們的,那只是你們通過非法手段,竊取了這個國家的權力,你不是民選的。你口口聲聲說你是為了人民,實際上人民一直被你奴役著。可是用各種鋼絲、綁繩、手銬,改變不了人心。越這麼做,時間越長,越是觸及不到人思想靈魂上真諦的東西,結果適得其反。
我母親1974年就故去了。母親走後,我把家歸置歸置,沒事就東遛遛西逛逛。1976年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倒台,據說廠子裏開了一次大會,宣布徹底給我平反。那天我正好沒在。我沒有任何激動,感恩。
你說給我平反,賞賜我點甚麼,我從此斷絕這一塊,我不讓你來這個!我是天地間一個獨立的個體,遵從天地人的法則,具有頂天立地的人格。我決定從此彰顯自己的個性,有尊嚴地活在世上。
這時期我想的最多的是,我往後這輩子應該怎麼活呀?我得安排我的事情,做點甚麼。
告別體制 不食周粟
1977年恢復高考,原來跟我一起蹲牛棚的北航崔教授說:「你報考我的研究生吧,作為導師,我有這個權力,你報我馬上就能讓你來。」
我參加了研究生考試,很有信心地等入學通知。因為我在文革時買了很多書自學,加上名師的指點,肯定比別人成績好。可等來的卻是,招生辦老師告訴我:你的政審沒通過。北航屬於軍工系統,政審很嚴。
工廠知道我參加高考,不願意讓我走。有一天我跟車間主任說:「明天我就不來了。」他以為我臨時有甚麼事請個假呢,說:「你去吧。」按他們的意思,我應該完成個甚麼手續,我的人事檔案關係還在他們那兒呢。可是我從根兒上就不承認那個東西,我也不歸你管,我不要了!就這樣告別了這個體制,從此再沒進去過。
我放棄了獲取文憑這條路。在共產黨的天下,家裏有歷史問題,要文憑有用嗎?最後,還是在華羅庚先生的幫助和引薦下,我進入到科研系統,做過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的評論、中國汽車工業發展的政策研究,參與了中國科技諮詢服務中心的籌建,還做過科學技術的預測等等。我個人的興趣還是在具體的專利、設計方面,所以後面幾十年,我等於成了科技專業戶,做了很多高科技研發的大項目,與不同單位、不同地域進行過跨越不同科技領域的合作,涉及很前沿的創新,到哪都是擔任總工程師。
這一切都受益於文革期間從華羅庚、錢學森、北航的崔教授等先生那裏打下的基礎,打的比較深遠、深厚。
直到現在,我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地方,走了自己的一條比較艱辛但自由的路。我在共產黨非常高端的機構裏幹過好多事,但是我從來不粘你們一點東西。我一不要你們的勞保,二不要你們的待遇,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養活自己和家庭。我就相當於古人的「不食周粟」。你們認為我應該按照你們的要求愛你們的黨,愛你們的國,愛你們的政府,我沒那個義務。
尾聲
1978年的一天,我正在樓下跟幾個高中孩子聊天,前邊開過來一輛車,停得遠遠的。從車上下來一個老太太,走到我跟前。我說:「您是找我吧?」她問:「你是李XX吧?」我就帶她回家了。其實我知道她是誰,我有感覺,她是我的五姨。我等著她說,但是她不說,她只說,「我來看看。」我說:「我媽已經去世了。」她說她知道。我告訴她,我也辭職不幹了。
她說她在東北,我估計,可能是從撫順戰犯管教所出來的吧?她為甚麼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來?是沒解除管教,還是就業了?我不敢直接問她。
我怕共產黨讓她帶著竊聽器,記錄下來對她也不好。我說,您就自己照顧好自己,我自己這都好辦。沒說幾句,她就走了。平時根本沒來往,後來也沒再來往,她也沒說明來意。我估計中共是想讓她驗證一下,我是不是那個李北海。那個車肯定是公安局給找的。
我結婚多年後,妻子因信仰被拘捕。警察審訊她時說:他們懷疑我是台灣特務!時間已經來到2000年以後了,他們還在懷疑我。
編後記
整理完李北海先生錐心泣血的自述,不禁掩卷長嘆,它堪稱一部中共統治下中華民族受難的縮微史,又是一部中國人的個人心靈史。感謝他,在時間的流水還未來得及沖淡記憶之前,為我們留下了這篇寶貴的歷史記實,以及每一個節點上的深入思考。
對於從未在中共治下生活過一天的台灣人來說,包括1949年離開大陸的國民黨一代、二代,對於已經習慣了中共的話術、自願或無奈地順從著中共極權控制的大陸人來說,讀這篇回憶,無異於一副醒腦劑,一本教科書,提醒我們不要忘記,中共奴役人、毀滅人的本性是在骨子裏的,永遠不會變。#
(全文完)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