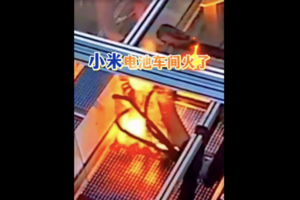50年前在中國河南省駐馬店地區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悲劇,板橋、石漫灘共62座水庫大壩相續發生潰壩(以下簡稱板橋潰壩事件),造成24萬人死亡。
板橋潰壩五十年後的今天,想談的東西很多,最後決定還是回到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天災人禍。中國河南省駐馬店地區發生的板橋等62座水庫大壩的潰壩災難,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在蘇聯史太林主義的指導下,在淮河上游建造了板橋、石漫灘、薄山等五座大型和很多中小型水庫大壩工程,其目的就是駕馭自然。但是缺乏建設大壩工程所需要的氣象、水文等基礎資料,板橋、石漫灘水庫都在很短的時間內竣工。1954年淮河流域發生了四十年一遇的洪水,這才發現水庫大壩工程的防洪設計出錯。於是在1956年底前實施了擴建加固工程,抬高水庫大壩的頂高和加大泄洪設施的能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又一次對大壩工程進行調研,發現防洪設計還是有錯,建議再次擴建。但是這一次的擴建加固工程並沒有得到實施,據說原因是「時值十年動亂」。
1975年8月4日至8月8日凌晨,水庫大壩所在的駐馬店地區降下暴雨,板橋、石漫灘等62座水庫大壩發生潰壩。在潰壩發生之前,板橋、石漫灘等水庫起碼還有兩次機會,可以避免潰壩的發生、減少死亡人數。可惜,這些機會也被錯失。
首先,水庫大壩工程建設時缺乏最基礎的數據,導致工程完工後一改再改,最終也沒有達到防洪安全的要求,為潰壩埋下了禍根。其次,在應對暴雨、洪水的過程中,管理混亂,管理者迷信銅牆鐵壁的大壩是不會垮塌,就像相信樓價只漲不降一樣,應對一錯再錯,直至世界十大技術災難之首的悲劇發生。板橋等62座水潰壩是天災還是人禍的問題,答案十分清楚。
一、天災人禍
天災人禍是一個成語,最早出現在元代戲劇《馮玉蘭》中。這個成語出現在元朝,而不是之前的漢朝或者唐朝或者宋朝,是有原因的。元朝是外族入侵,中國百姓不滿,文人通過戲劇罵罵老天,當權的不知是罵皇帝的老子,這樣的戲曲也還可以在民間流傳。
天災指自然界發生的異常或者極端現象,如強降雨、乾旱、地震、地面開裂、滑坡、岩崩、山火、海嘯等等;人禍指由於人類活動所導致的災難,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國出現的大饑荒和人口的大規模減少,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中的「文化大革命」,如2005年6月10日黑龍江寧安市沙蘭鎮小學超過百名學生老師死於潰壩洪水,又比如剛剛於2025年7月28日發生在北京密雲養老中心31位老人的遇難……
按照中國儒家「天人合一」的觀點,發生地震、大旱、暴雨等自然災害,都是上天意志的體現。皇帝作為天子(上天的兒子)來管理眾生。天子掌權的正當性就來自老天的授權,而不是全民的選舉。天子又稱王,王的寫法是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天地人之間的訊息傳通,只有天子有這種特殊的功能。清朝的皇帝每年到天壇去祭天,求今年風調雨順,有個好收成。為甚麼要皇帝施行這個祭天形式,因為皇帝作為天子能上情下達或者下情上達。但是如果天子失德,管理失調,上天就通過自然災害給予警告。如再發生重大災害,這個皇朝也該壽終正寢了。公元前780年,陝西岐山發生大地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國語》)。《詩經‧周頌‧敬之》說,不要說老天高高在上,它日夜看著眾生。
二、對自然而言 沒有所謂的自然災害
對自然而言,無論是經常出現的狀態還是罕見的極端現象,都是自然現象,不構成對自然的任何危害,是自然界去舊換新的必須。
比如洪水,這是自然界會循環發生的現象。埃及人很早就觀察尼羅河水位的變化,記錄洪水水位線,那時人們對洪水的評價是正面的。尼羅河年復一年發生的洪水,帶來大量的泥沙和沉積物,洪水越過高度不大的自然河堤,把含有大量有機物質的泥沙沉積物覆蓋在河邊的農田上,保持或者補充了土壤的肥力。洪水退去後,農民在「施了肥」的農田上播種,可以獲得好的收成。希羅多德的《歷史》中也描述了古埃及人利用尼羅河氾濫進行農業生產的方式。中國著名作家鄭義也觀察到這種情況,在論述1975年板橋潰壩事件的文章中寫道:大水之後的第二年,這片埋葬了無數生靈的土地,麥子長得格外茂盛。
多德蒙特大學空間規劃系區域發展和災害管理專業的司戴方‧格萊峰(Stefan Greiving)教授認為,自然河流流量的周期性的變化是自然現象,洪水就像婦女的例假一樣,不可能消滅的。洪水是自然界去舊換新的一個過程。
三、中共向老天宣戰 要消滅自然災害
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之後,就邀請蘇聯專家來華指導,或者更可能,是蘇聯史太林主動派出專家來制定全中國各個大河流流域的治理規劃。毛澤東也不時地發出號召,今天要治理淮河,明天要修理黃河,後天要把長江的事情辦好,接著要根治海河……
我是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這是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的三個問題。
那麼1949年10月1日後直至今日,中共治水的目的是甚麼?這些理念來自哪裏?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這也是關係到板橋潰壩事件的三個問題。
這裏引用當年的副總理鄧子恢1955年7月18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向全國人民代表解釋治理黃河規劃和建造三門峽水庫大壩工程的一段話,它可以回答上述的問題。
鄧子恢說,史太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在上古時代,江河氾濫、洪水橫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莊稼的毀滅,曾認為是人們無法避免的災害。可是,後來隨著人類知識的發展,當人們學會了修築堤壩和水電站的時候,就能使社會防止在從前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不但如此,人們還學會了制止自然的破壞力,可以說是學會了駕馭它們,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我們今天所要做的工作正是如此。
鄧子恢還說:「我們的任務就是不但要從根本上治理黃河的水害,而且要同時制止黃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和消除黃河流域的旱災;不但要消除黃河的水旱災害,尤其要充份利用黃河的水利資源來進行灌溉、發電和通航,來促進農業、工業和運輸業的發展。總之,我們要徹底征服黃河,改造黃河流域的自然條件,以便從根本上改變黃河流域的經濟面貌,滿足現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和將來的共產主義建設時代整個國民經濟對於黃河資源的要求。」「黃河的災害同反動統治階級的罪惡是分不開的。」
可見,中共治理河流的理念和方法,都是來自史太林,來自蘇聯,不但要消滅洪災,而且要消滅旱災,還要利用黃河的水利資源來進行灌溉、發電和通航,實現共產主義。
消滅水災!消滅旱災!消滅自然災害!人定勝天!向老天宣戰!當年河南省主要負責人吳芝圃是最積極的吹捧者和執行者,提出了「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據說吳芝圃是毛澤東湖南農民講習所的學員。
具體的做法就是大量修建水庫大壩工程,不但要建設大型、中型的水庫大壩,還要大量地建設小型的水庫。1950年8月25日至9月12日,中共政府召開治理淮河會議,會議決定以蓄泄兼籌為治淮的方針,並確定淮河上游以蓄洪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中游以蓄泄並重,下游則開闢入海水道。1950年10月14日中共政務院作出了《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淮河上游以蓄洪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就是建設水庫大壩蓄水,用於防洪、發電、灌溉等多重目的。河南省境內的淮河上游,在蘇聯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建造了板橋、石漫灘、薄山、白沙、南灣五座大型水庫和一大批中小型水庫。
四、板橋潰壩的主要原因
板橋潰壩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特大暴雨,由1975年3號颱風「妮娜」帶來的暴雨;
第二:大氣環流;
第三:地形的影響;
第四:氣象預報不準,更準確地說,中央和地方氣象部門都沒有做出預報;
第五:水庫運行出錯,暴雨發生之前是乾旱,農作物缺水,暴雨到來前期採取蓄水,致使蓄水超量;水庫管理者迷信大壩的堅固;
第六:淮河流域水庫大壩工程滿天星、葡萄串的布局,導致多米諾骨牌倒塌的效應;
第七:水庫設計的錯誤,暴雨、洪水的基本數據沒有或者不準,將責任推給蘇聯專家,指責搬用了蘇聯制定的防洪安全標準太低;
第八:發現防洪安全標準太低的問題後,未及時、果斷加以解決;
第九:水庫大壩工程質量差,如泄洪閘門被銹死,無法開啟等;
第十:水庫上游和周圍地區的森林覆蓋率低,水土流失嚴重;
第十一:通訊中斷;
第十二:等待最高領導作出決策,延誤了時機等等。
AI給出的一個答案是:總而言之,板橋水庫潰壩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因素,其中特大暴雨是直接誘因,而泄洪能力不足和管理問題是導致潰壩的關鍵原因。
五、水庫大壩的防洪標安全標準太低
本文主要討論水庫大壩的防洪(安全)標準和暴雨洪水期間水庫運行應對的問題。制定水庫大壩工程的防洪標準,是工程規劃和工程設計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水庫大壩的(防洪)安全標準太低所導致的問題就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建造水庫大壩工程的基礎是氣象、地質、水文、地理數據。在淮河上游建造五座大型水庫和一大批中小型水庫,缺乏必須的基本數據,最長的實測數據也只有兩三年。當時大學肄業的錢正英是治淮委員會的負責人,是最主要的技術力量。1975年8月8日板橋等水庫潰壩後,當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電部在鄭州召開全國水庫安全會議,時任水利部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錢正英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興建時水文資料很少,洪水設計成果很不可靠」。板橋、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就是在這樣的數據基礎上建造的,就為後來的潰壩埋下了禍根。張建雲、楊正華和蔣金平在《我國水庫大壩病險及潰決規律分析》一文中指出:設計施工失當。20世紀特殊年代興建的工程先天不足是較普遍現象,抽樣統計,未進行地勘或勘探粗淺佔20.0%,未設計或邊施工邊設計佔6.7%,未清基或清基不徹底佔46.7%,施工質量較差佔70.0%。
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位於淮河支流洪河的支流滾河上,壩址所在地現屬舞陽市。建設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的目標是多重的,防洪、為工業供水、灌溉、發電等。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壩型為均質土壩,壩長500米。據說防洪標準按50年一遇設計,500年一遇校核,水庫總庫容4700萬立方米。因為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是淮河流域上游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水庫,有「治淮第一壩」的美稱。工程於1951年4月1日開始建設,7月24日水庫竣工運行,總施工時間不到4個月。
位於淮河支流汝河上的板橋水庫大壩工程於1951年4月開工建設,1952年6月竣工,全部建設時間為14個月。建設板橋水庫大壩工程的目的是以防洪為主,兼顧灌溉、供水、發電、漁業生產等。板橋水庫的庫容比石漫灘水庫大,它的防洪標準也要高一些,按100年一遇設計,1000年一遇校核。
1954年7月淮河流域發生40年一遇的洪水,這是老天爺對淮河上游水庫大壩工程的第一個警告。石漫灘、板橋、薄山等水庫實際最大入庫洪水量,超過了原設計的標準一至三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通過1954年的洪水才發現,原來建設大壩水庫工程時所使用的數據十分不靠譜,可以說許多數據是拍腦袋想出來的,或者是隨意畫出來的,比如暴雨頻率曲線就是畫出來的。
經過1954年7月大洪水數據的校正,洪水標準再次按照蘇聯水工建築物國家標準進行設計,對工程設計進行了修正。
石漫灘水庫按2%頻率設計,0.2%頻率校核(即50年一遇設計、500年一遇校核),校核頻率3天降雨486毫米,洪峰流量1675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0.88億立方米。據此,確定大壩加高3.5米,壩頂高程達到109.7米,防浪牆頂高程111.2米。經過加固,最大庫容為9440萬立方米,其中調洪庫容為7040萬立方米,最大泄量390立方米每秒。
板橋水庫採用1%頻率設計,0.1%頻率校核(即通常所說的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校核頻率3天降雨量530毫米,洪峰流量5083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3.3億立方米。據此,決定大壩加高3米,壩頂高程為116.34米,防浪牆高程為117.64米;增闢輔助溢洪道,寬300米,底部高程為113.94米,連同原有的溢洪道、輸水洞,最大泄洪能力為1742立方米每秒,最大庫容4.92億立方米,其中調洪庫容3.75億立方米。經過擴建之後,板橋水庫大壩工程被譽為安全性能非常好的「鐵殼壩」,被認為是可以抵禦百年一遇的洪水,即使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也是安然無恙。
石漫灘、板橋、薄山、白沙水庫均在1956年年底前完成擴建加固工程。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共與蘇共翻臉,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水利部組織專家又對石漫灘、板橋等水庫大壩工程進行檢查覆核,發現擴建之後的工程依然不能滿足規定的水庫大壩工程的防洪標準。
專家對照1954年擴建時的數據,如果板橋水庫大壩工程要達到按百年一遇設計、千年一遇校核的防洪標準,板橋水庫大壩工程必須能抗住3天637毫米的降雨所產生的洪水,計算來水量4.3億立方米,而不是過去說的能抗住3天530毫米的降雨,計算來水量3.3億立方米。建議板橋水庫大壩還需要再加高0.9米。
如果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要達到按五十年一遇設計、五百年一遇校核的防洪標準,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必須能抗住3天738毫米的降雨所產生的洪水,計來水量1.46億立方米。而不是過去說的能抗住3天486毫米的降雨所產生的洪水,計來水量0.88億立方米。建議石漫灘水庫大壩要再加高6.4米。
但是這只是水利部內部的一個研究調查報告,沒有對外公布,更沒有像1954年7月大洪水後對工程實施了擴建和加固。雖然水利部領導知道,淮河上游的這五座大型水庫工程都存在嚴重的安全風險,但是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的「治淮第一壩」的美稱與板橋水庫大壩工程的「鐵殼壩」的美名依然存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專家們發現板橋、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的安全隱患,也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措施,但是水利部革命委員會並沒有落實實施。為甚麼?錢正英在重建板橋潰壩大壩的碑文中寫得很清楚:「時值十年動亂……」這就算給出了解釋。
老天給了第二次機會,錢正英沒有把握,卻把責任推給了時間,「時值十年動亂……」,推卸責任的水平非常之高。
中共取得政權後匆忙建造大量水庫大壩工程,但又缺乏暴雨、洪水基礎數據,導致防洪標準設置過低,致使水庫大壩工程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中共解決的辦法是兩個:第一,加大壩高或者提高蓄水位,增加庫容;第二,擴大泄洪能力,如擴建泄洪設施。這兩種辦法在都實踐中都得到廣泛應用,如剛剛泄洪造成人道災難的密雲水庫,幾十年來就一直在增加泄洪能力。又比如三峽工程,蓄水位可以從正常蓄水位175米升高到180.4米(高程)。通過這樣的辦法,使得水庫能夠排泄最大的洪水流量,就是進來多少水就能排泄多少水,以此來保證大壩的安全。請讀者這時暫停幾秒想一下,這時的大壩防洪效益為零或者為負。
六、75.8暴雨過程中錯失機會
1975年8月5日至7日,河南省西南部山區發生了一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無論是中央氣象台站還是地方氣象台站,對即將發生的暴雨都未做出預報。
但是,老天還是給出了災難即將到來的訊號。有人已經觀察到,不祥徵兆在天地混沌的狀態下陸續出現了。8月4日,橋板鎮,雞不入舍,豬不吃食,一黃狗跳上屋頂,如狼狂嘯;橋板水庫下游幾十里處的暴雨核心點林莊,村邊聚滿了黑壓壓的烏鴉,驅不走、趕不散,聒噪不已。上游泌陽縣境內大路上螞蟻密密麻麻地搬家。自然災害前會出現一些異常的徵兆,這不是迷信,而是許多民眾和科學家對自然界仔細觀察得到的結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
這是老天的第三次警告,人們忽略了。
75.8暴雨中心3天降水總量1605毫米,24小時最大降水量1054.7毫米,6小時最大降水量為685毫米,1小時最大降水量189.5毫米。其中1小時和6小時最大降水量均創造中國歷史上最高紀錄。
分析暴雨,各種時間段的暴雨量固然很重要,對於水庫大壩工程來說,暴雨範圍的大小是同樣重要。
上圖是1975年8月5日至7日三天雨量的分布圖。最強暴雨帶位於伏牛山麓的迎風坡,即洪汝河、沙潁河、唐白河上游的板橋、石漫灘兩大水庫地區及其周圍。暴雨中心在板橋水庫附近的林莊,石漫灘水庫附近的油坊山以及郭林,中心最大過程雨量分別為1631毫米、1434毫米、1517毫米。400毫米以上的雨區面積達19,410平方公里。大於1000毫米的暴雨區在京廣鐵路以西薄山水庫西北經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到方城一帶 。
75.8暴雨由三場暴雨組成。第一場出現在5日14時至24時;第二場出現在6日12時至7日4時;第三場暴雨出現在7日16時至8日5時。其中以7日暴雨最大,5日次之,6日最小。7日暴雨不僅範圍廣,強度大,而且50%至80%的雨量又集中在最後的6小時,例如7日最後6小時雨量達685毫米。
75.8暴雨由三場暴雨組成,三場暴雨之間有兩次12小時的間歇,雨量變小或者降雨停止。如果上級水利部門或者水庫管理部門利用這兩次間歇,加緊泄洪,哪怕是檢查一下泄洪的閘門是否能夠開啟,那麼最後的結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再說板橋水庫的泄洪能力為每秒1742立方米,24小時可以泄洪1.5億立方米。如果當時果斷地啟用泄洪設施,這場潰壩應該可以避免。
石漫灘水庫大壩發生潰壩的時間是8月8日零時30分,板橋水庫大壩發生潰壩的時間是8月8日1時左右。在石漫灘、板橋水庫潰壩前,也就是在7日21時前,確山、泌陽已經有7座小型水庫垮壩,22時,中型水庫竹溝水庫垮壩。潰壩洪水加大了由於暴雨而產生的洪水,入庫的洪水流量是自然洪水和潰壩洪水流量的疊加,是人為因素加大了洪水流量。這種人為因素加大洪水流量的惡性後果是來自所謂的水庫滿天星、葡萄串的布局,也就是現在所謂的河流梯級開發。
從時間上來說,7日21時前確山等7座小型水庫潰壩,到石漫灘水庫和板橋水庫潰壩還有3個半小時和4個小時以上的時間,可進行最緊急的處理。最簡單也是最起碼要做的,就是通知下游的居民離開危險的區域。可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通知居民撤離。
其實當時水利部門或者水庫管理部門從來都沒有考慮到這麼一個常識性的問題:水庫大壩會潰垮!大壩潰垮會產生潰壩洪水,潰壩洪水的流量、流速和破壞力,都是自然洪水無法相比的。他們還沉浸在「鐵殼壩」、「淮河第一壩」的讚譽聲中!所以他們也沒有想到要泄洪,也沒有想到要事先檢查一下泄洪設備是否能正常運用。人們又錯過了老天給的第四次機會。
回到防洪標準上來。在淮河上一起建造的五座大型水庫中,板橋、石漫灘兩座水庫大壩工程發生潰壩,薄山、白沙、南灣三座水庫大壩工程得以倖免。
石漫灘水庫發生潰決時,水庫的壩前水位111.40米(高程),超壩頂1.57米。
經過1956年的擴建加固工程,石漫灘水庫壩頂高程達到109.7米,防浪牆頂高程111.2米,只比壩前水位111.40米低0.2米。如果採取一些泄洪措施,緊急用沙袋加固加高防浪牆頂高程,不至於造成潰壩。如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專家認為石漫灘水庫的大壩還要再加高的意見得以實施,也不會有潰壩事件的發生。
板橋水庫發生潰決時,水庫的壩前水位117.94米(高程),超壩頂1.6米,超壩頂防浪牆0.3米。
經過1956年的擴建加固工程,板橋水庫壩頂高程為116.34米,防浪牆高程為117.64米,只比壩前水位117.94米低0.3米。如果採取一些泄洪措施,緊急用沙袋加固加高防浪牆頂高程,也不至於造成潰壩。如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專家認為板橋水庫大壩需要再加高0.9米意見得以實施,也不會有潰壩事件的發生。
對比在75.8暴雨洪水中沒有潰壩的薄山水庫大壩工程,1975年8月8日3時,壩前洪水已經上漲到超壩頂0.4米,距離防浪牆頂只有0.6米。在水庫職工、家屬、駐水庫舟橋部隊、薄山林場職工以及趕來搶險的山炮兵第2師官兵40個小時搶救,堵住了防浪牆滲水,並在壩頂築起了2米高子堤,保住了薄山水庫。當年的調查報告沒有涉及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同在暴雨中心的薄山水庫能保住,而板橋和石漫灘水庫卻不能?
七、板橋潰壩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1975年8月8日發生了板橋潰壩事件。那麼中國民眾是甚麼時間知道這個特別重大事故的呢?
從1975年8月8日到1987年8月,中共政府並沒有將板橋潰壩事件告訴中國民眾,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沒有公開報道此事。如果沒有三峽工程的爭論,這個悲劇可能至今還被一直隱瞞下去。是三峽工程反對派在工程可行性論證爭論中,向外界公布了此事件。
1987年8月八名第6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孫越崎、林華、千家駒、王興讓、徐馳、雷天覺、喬培新和陸欽侃聯名撰寫題為「三峽工程害多利少,不容欺上壓下,禍國殃民」的文章,文章在論述三峽大壩工程的防洪效益與大壩安全時寫道:「建這樣一個大壩,他們是不是不知道這中間存在著重嚴重問題呢?不是的!他們很清楚……(二)1954年長江大水死人3萬。淮河上游河南舞陽縣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庫容只有6億立方米,1975年8月失事,猛衝下去,死人23萬左右。這個對比很清楚,1954年長江大水死人數反而成了個零頭……」
陸欽侃等的文章第一次公開揭露板橋潰壩事件造成23萬死亡。之後一些海外新聞機構予以轉載,特別是幾個香港的雜誌和報刊。
2005年5月美國探索頻道節目《終極十大》將板橋潰壩事件評為「世界十大技術災難」(The Ultimate 10 Technological Disasters)的第一名,超越蘇聯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報道指出,死亡人數為24萬。
2005年11月26日新華社發表題為「30年後,世界最大水庫垮壩慘劇真相大白」的報道,應該是新華社公開發表的第一篇關於板橋潰壩事件的報道。報道中稱,超過2.6萬人死難。如這篇報道題目所揭示的,這場世界最大的水庫垮壩慘劇被隱瞞了整整30年,而且對死亡人數還是遮遮掩掩。
上面已經分析道,老天給過四次警告,如果予以重視,不會有此場悲劇。就是利用暴雨發生後的間歇時間,利用泄洪設施泄洪,也不會有如此悲慘的結果。最後在得知有七座中小型水庫潰壩的消息後,立即通知下游居民撤離,起碼還能挽救大部份遇難人員的生命。
中共政府至今也沒有公開死亡人員的姓名。據筆者所知,政府有統計的名單,有死亡人員包括名字、性別、年齡等具體數據。為甚麼不給死難者建立一個紀念碑,刻上死難者的名字?
八、結束語
1986年板橋水庫大壩工程實施重建,1993年6月5日竣工。1993年9月15日石漫灘水庫大壩工程實施重建,1998年1月9日竣工。
1975年8月8日發生板橋等62座水庫潰壩的遺蹟如今已經被抹得乾乾淨淨。站在重建的板橋和石漫灘水庫大壩前面,人們看到的是水庫碧波萬頃,景美如畫,難以想到1975年8月8日的潰壩事件,更難想起24萬失去的生命。
2024年筆者在去意大利旅遊時路過位於威尼斯北部多克山中的瓦伊昂大壩。十分遺憾,沒有能夠去大壩去弔念一下,可惜沒有趕上可以參觀的時間。瓦伊昂大壩始建於1957年,完工於1959年,壩高262米,是當時世界上壩高最高的大壩,也代表了當時最最先進的技術。1963年10月9日庫區發生大規模滑坡,滑坡進入水庫,將5000萬立方米的庫水擠出水庫,庫水從大壩上方飛過或溢過大壩。結果大壩完好無損,但是飛躍而下的洪水造成大壩下游2018人的喪生,其中487人是年紀15歲以下的兒童。有媒體把瓦伊昂大壩的失事排為世界水庫大壩失事的第二位。
如今瓦伊昂水庫已經早被廢棄,是一個乾庫,失去了發電、供水等功能。但是大壩依然保留在那裏,作為參觀憑弔的地方。每年有幾個月的時間可以預約參觀,有導遊詳細介紹事故發生的過程和原因。這麼做的目的是為甚麼?難道不知道這個完好無損的大壩還有繼續利用的價值?目的非常明確,為了不忘卻!為了類似的悲劇不再重演!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