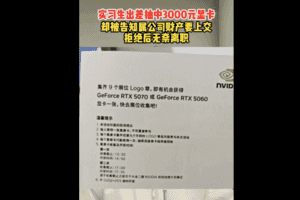11月8日至15日的紐約,本應是「IndieChina電影節」在紐約布魯克林登場的一周。綠點區一處小型文化空間,早已掛上「IndieChina Film Festival」的海報。這是該影展的第一屆,由獨立策展人、導演朱日坤主導,準備放映40多部關於中國的獨立電影,並邀請22位導演到場交流。
然而,距離正式開幕僅剩兩天,11月6日凌晨,朱日坤緊急宣布:電影節取消。所有公開放映、論壇、工作坊全面停辦;已售出的門票全額退費;場地改為私人聚會,不再對外開放。
這場原本默默無聞、規模不過數十人的活動,卻突然捲入一場跨國壓力的風暴。一張看不見的網,從北京深夜到紐約清晨,迅速收緊──最終,它成功讓中國的獨立創作者噤聲,讓在美國的華語文化活動停擺,甚至無需一紙正式的警告或說明。
一、清晨五點的電話
事情的轉折始於10月30日的一通電話。
那天清晨五點,朱日坤的父親突然來電,語氣異常,問他「是不是在外面做了甚麼不好的事」,並叮囑他「不要在外面做對國家不好的事情」。
他還來不及釐清原因,北京又傳來另一個訊息:一位臨時借住在他工作室的女租客告訴他,她被「有關部門」帶去談話,被要求不得再幫他處理雜務,還親耳聽到一句:「等他回國,一定要法辦他。」
她被明確要求把此事告知朱日坤,並向部門回覆。
在中國的政治語境裏,這些話的含義再清楚不過。
二、接連消失的導演們
在接下來的兩天內,幾乎所有還在中國境內的導演都來信取消參展。理由幾乎一模一樣——「個人原因」。要求撤片、撤宣傳、撤名字,甚至要求刪除社交平台上所有與其影片有關的任何蛛絲馬跡。
有人不敢多說一句;也有人明白告訴他,他們或家人被要求退出。
壓力並不侷限於中國境內。身在歐洲、美國、非洲等地的導演也陸續告知:因家人被查詢或「被談話」,不得不撤片。連主持映後座談的影評人、論壇嘉賓,其在中國的家屬都遭受干擾。
朱日坤原以為只是個別事件。然而,幾天內情勢急轉直下,名單上的名字一個接一個消失,彷彿骨牌倒塌般無法阻擋。當撤片比例逼近九成,連原本熱切期待的嘉賓也開始人心惶惶。
三、滲透進紐約的匿名信
威脅並非只來自千里之外。
其中一處紐約放映場地收到署名「一群生活在紐約的中國學生」的匿名電郵,指控影展將放映的影片「可能無法準確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要求取消所有活動。
朱日坤在接受英文新唐人採訪時說,他從未收到任何正式通知:「我沒有得到任何直接的訊息,沒有人直接找我說哪一部片敏感,也沒有人說你因為某部電影有問題。」壓力不是針對他,而是針對導演、家屬、嘉賓、義工及協助者──只要和影展沾上邊,就會變成施壓對象。當他意識到參與者的風險已無法控制,電影節已難以為繼。
收入方面更是全面崩盤:原本希望靠售票和周邊商品回收部份成本,如今不僅毫無收入,還需要全額退票、支付額外手續費。大量已訂票、從加拿大、歐洲甚至中國飛來觀影的觀眾,也因此蒙受損失。朱日坤表示,就連在美協助他的義工也因家人遭到威脅而被迫退出,使所有後續處理工作都落在他一人身上,信箱裏堆滿各種信件,僅是近40部影片導演撤映所牽涉的流程,就已是龐大工作量。
「壓力是滿分10級。」他說。
四、無資金靠山的「威脅」?
一個小型、低預算、僅有數十人規模的影展,為何會引來如此大規模施壓?
朱日坤說,所有影片都是獨立創作,「Indie China電影節」也完全靠他個人資助:場地、住宿、宣傳、交通等費用加總約5萬美元,而眾籌僅募到約1100美元。他估計每場放映約60至70名觀眾──這是一場以理想支撐的獨立行動。
如此小型的活動竟受到跨境施壓,讓朱日坤感到荒誕。他說,原本只想放映幾部熟識導演的作品,但公開徵件後,意外收到世界各地近200份投稿,題材多元,展現出華語創作者創作的力量,讓他感到「鼓舞」。
最終入選31部作品, 加上特別節目共約45部,形成一個難得的華語獨立影像縮影。
影展片單包括描繪中越邊境兒童處境的《山火再燃燒》,以及香港導演梁思眾與李成琳拍攝、記錄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血在燒》(If We Burn)——一部常被外界簡化為「抗爭片」的作品。但朱日坤認為,不應以刻板視角來看待這些電影。
他強調,自己反對為影片貼上單一、絕對的定義,也不願讓作品被概念化或標籤化。「對我們來說,電影本來就是多元的。不同觀眾會有不同的理解與感受,每個人都能從作品中獲得不一樣的訊息。」
對他而言,好的電影不該只服務於某種立場,而是允許觀眾看見「複雜的真實」。影展旨在打造良性交流的空間,讓香港、貧困、移民議題,乃至日常生活的細微感受,都能被自由展現。
但也正是這些影片呈現真實生活與社會矛盾、觸及敏感議題,才無法在中國上映。在中國,電影依《電影產業促進法》必須送審並取得龍標,在中國從事電影工作被要求「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沒有龍標的作品不能上映,也不能參加影展。
五、被封殺的獨立電影節史
49歲的朱日坤生於廣東,畢業於北京大學,曾擔任多個國際電影節評委。這不是他第一次面對審查。
2014年從中國搬到紐約之前,他在中國策劃獨立影展近20年,也是「北京獨立電影節」的共同創辦人。十多年來,影展在中國屢遭驅散、取消、場地被封、硬碟被沒收。
人權觀察(HRW)指出,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國的自由空間迅速收縮,三大獨立影展——北京獨立電影節、中國獨立電影節(原雲之南)、雲之南紀錄影像展——全被取締。
北京最後一次獨立電影節遭關閉時,中共官方切斷電力、沒收檔案,並要求主辦方簽署承諾書不得再舉辦影展。許多組織者試圖將形式改為在多個場地放映,但沒有成功。
朱日坤坦言:「最終,我所有的影展都被禁止,沒有一個能繼續。」
即使如此,他仍相信總有一個地方能舉辦真正自由的「IndieChina電影節」。那個地方,他以為是紐約。
然而,他萬萬沒想到,審查會跨越太平洋,直達布魯克林街頭。
六、審查跨海而來
人權觀察中國問題研究員尤魯永(Yalkun Uluyol)指出,中國政府「把手伸到世界各地」,企圖藉此控制全球怎麼看待、理解中國。
這類跨境恐嚇並非新鮮事──過去幾年,海外華語文化圈和學術社群一直面臨各種形式的跨境施壓,形式包括對家屬的壓力、對異議者的監看、留學生社群的動員、匿名恐嚇,以及舉報與騷擾等。
朱日坤這次遭遇的,是這些手法的集中展示。
尤魯永認為,海外政府應當正視這些跨境干擾言論自由的跡象,並提出因應。《紐約郵報》的社評也以強烈語氣批評此事,認為外部勢力能夠有效影響紐約的文化活動與言論空間,值得各級政府警惕。並主張美方應對相關行為提出明確回應,以維護自身的價值與利益。
七、取消,是唯一能保護他人的方式
面對不斷湧來的壓力,朱日坤放棄了籌備大半年的心血,被迫做出「異常痛苦」的決定:取消影展。
「我很痛苦,但如果不停下,任何參與者——導演、論壇參與者、外圍人士、義工、甚至觀眾——都有可能受到威脅或者騷擾。這種情況,導致我處於艱難的倫理境地。我們需要對別人的安全負責。」
在Facebook上公布取消聲明後,他寫道,自己「並非出於害怕或屈服而作出(取消電影節的)決定」,但希望某些「不明勢力」不再騷擾和電影節有關的人員。
他強調,取消並不代表結束。
取消後,場地租金已無法退還,他仍每天前往空蕩的放映室,獨自放映、與友人討論。他說:「這也是一種藝術行為,是一種抵抗。」
八、獨立電影節的價值
朱日坤一再強調,獨立電影節不是挑釁,而是希望提供一個讓多樣敘事共存的平台。「獨立」意義在於創作者不必迎合任何權力。
在高度審查下的商業電影,往往只能呈現單一、安全、避開敏感議題的敘事;角色扁平、問題被遮蔽。
他說:「獨立不是一定好,品質參差、技術不成熟、表達過度生硬等問題都存在。但它讓真實、多樣、帶傷口的故事有存在的可能。」
例如他在2013~2014年拍攝《塵》,記錄塵肺病工人的生活──一旦罹患塵肺便不可逆,但若使用專業防護本可避免,但工廠卻推責;工人上訪遭監控與阻撓。正是這類真實又複雜的故事,無法存在於審查體制之中。
九、「第一屆」仍然存在
朱日坤認為,雖然影展被迫取消,但這一屆仍然「發生了」。
它成為一個歷史記錄——一個跨境審查抵達紐約的案例,一個渺小但頑強的獨立文化事件。他也宣布,明年會舉辦第二屆。
「我仍然是來自中國的獨立電影人。我不會停。」他說。#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