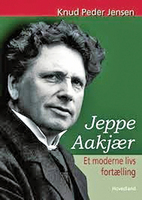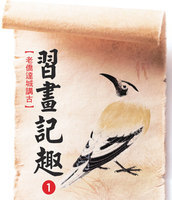視覺藝術與文學的交集,為創造力勃發提供著沃土。數個世紀以來,詩人、作家、畫家以及哲學家們一直在「對話」,回應著彼此的理念和藝術表達,這堪稱西方文明的一大瑰寶。每一件受到文學啟發的藝術作品,都評說著孕育它的作品:不僅詮釋作家的意象、為作家的作品增添深度,同時也成為一種新的意象——一件本身就是藝術的新作品。
對文學評論家和藝術學者們來說,探索這種藝術的對話會帶來滿滿的喜悅。在協同互惠的關係中,繪畫藝術為文學與詩歌增添光彩,反之亦然。
本文帶您領略藝術文學跨界互動的五個至為精美的範例。
《伊卡洛斯墜落時的風景》 老彼得‧勃魯蓋爾1560年作
荷蘭繪畫大師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約1525—1569年)的這幅畫可比作一棵樹的樹幹:它根植於文學傳統,又為後世文學作品開枝散葉奠定了基礎。畫中,勃魯蓋爾描繪了伊卡洛斯和代達羅斯(Icarus and Daedalus)神話故事的場景。

希臘神話中,天才工匠和發明家代達羅斯為克里特島國王米諾斯(Minos)建造了一座錯綜複雜的迷宮,用來囚禁牛頭人身怪物米諾陶(Minotaur)、讓它無處可逃。然而在代達羅斯完工後,米諾斯國王卻不許他和兒子伊卡洛斯回家,將他們鎖入一座塔樓。
為了帶兒子逃出生天,足智多謀的代達羅斯用羽毛和蠟造了兩對翅膀。然而伊卡洛斯忽視了父親的告誡,飛得離太陽太近了。蠟融化了,羽毛飄散,伊卡洛斯最終葬身大海。
在描繪伊卡洛斯墜海而逝的瞬間時,勃魯蓋爾進行了耐人尋味的布局。他將伊卡洛斯身體撞擊海面的一幕置於背景中,微小到連路人都不會注意到兩條細小的腿沉入碧綠的深海。勃魯蓋爾畫作的焦點是駛向大海的宏偉帆船,以及前景中在田間勞作的耕夫。
這幅名畫激發現代主義詩人奧登(W.H. Auden)創作了一首名詩(譯注1)。畫中的多數人物都對伊卡洛斯遭遇的悲劇茫然不知,引起了奧登的思索。他寫道:
說到苦難,他們從未看錯,
古代那些大師:他們深切體認苦難在人世的地位;
當苦難降臨,
別人總是在進食或開窗或僅僅默然走過……
就這樣,偉大的藝術在循環往復中孕育著偉大的藝術。
《安德羅瑪刻哀悼赫克托耳》 雅克–路易‧大衛1783年作
讀過《伊利亞特》的讀者,對史詩中最壯麗也最感人的情節之一——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Hector)和深愛他的妻子安德羅瑪刻(Andromache)的故事一定不陌生。赫克托耳是特洛伊王子,他堅守特洛伊城,抵禦希臘人的圍攻;憑藉領導才能、英勇氣概和作戰技巧,成為守城的基石。他還是一位細心體貼的父親和丈夫。
詩中最感人的場景之一,發生在一場戰役過後、赫克托耳重返特洛伊城探望安德羅瑪刻和兒子阿斯提亞納克斯(Astyanax)之時。他溫柔地與孩子玩耍,並且安慰妻子;妻子懇求他不要再回戰場。儘管她強烈反對,赫克托耳還是重返戰場——主要是為保護她的安全。
然而,最終他還是戰敗了,被阿喀琉斯的大手擊倒在地。大衛的畫作描繪了母子倆在赫克托耳屍首前悲痛不已的一幕。
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年)以精湛的技藝和悲愴的戲劇性描繪了這一場景,因此於1784年榮膺(巴黎)王家繪畫與雕塑學院(Académie Royale)院士。

在大衛的畫作中,最強烈的光線照射在傷心欲絕的安德羅瑪刻身上。她從赫克托耳的屍首旁轉身仰望上蒼。屍體半隱於陰影之中,從畫作左邊逼近的黑暗,彷彿死亡的陰副本身。
《莎士比亞〈麥克白〉中的宴會場景》 丹尼爾‧麥克利斯1840年作
丹尼爾‧麥克利斯(Daniel Maclise,譯註2)的這幅畫作充滿力量,以栩栩如生的光影運用、陰鬱的氛圍和戲劇性的人物姿態,讓觀眾為之屏息。
畫面描繪了莎翁劇作《麥克白》中,主人公看到自己殺害的昔日好友班柯鬼魂那一刻。在這位國王為貴族們舉行的宴會上,被害者坐在麥克白自己的王座上——當麥克白陷於夢魘般的嫉妒、偏執和殘忍時,班柯也未能倖免。麥克白看到幽靈幻象而受到了驚嚇。麥克白夫人立即向震驚不解的賓客解釋丈夫的怪異表現,這些客人看不到幽靈。

從吊燈上狂野的火苗,到麥克白夫人揮動的手臂和麥克白退縮的身影(與幽靈靜止的背影形成對比),這幅畫作擁有一種略顯失控的強大張力。它反映了麥克白開始無法控制局面時近乎瘋狂的狀態。
這是莎士比亞最黑暗的悲劇之一,畫作邊緣的陰影映襯出圍繞麥克白的陰暗、巫蠱與邪惡。麥克白夫人是畫中最耀眼的人物,這樣的構圖無疑反映了她對丈夫及劇中恐怖事件的重大影響。
《奧菲莉亞》 約翰‧埃弗雷特‧米萊斯爵士1851年作
莎士比亞的作品深受藝術家們鍾愛,這裏我們看到另一齣莎翁悲劇中的場景,這次是出自約翰‧埃弗雷特‧米萊斯爵士(Sir John Everett Millais,譯注3)的手筆。畫家淒美地刻畫了《哈姆雷特》中奧菲莉亞生命的最後時刻。
奧菲莉婭是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戀人。在父王的冤魂告知自己慘遭親兄弟毒殺後,哈姆雷特悲痛不已,舉止反常,還誤殺了戀人的父親——叔父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悲劇發生後,加之哈姆雷特棄她而去,使得奧菲莉婭精神崩潰。她在荒野中遊蕩,哼唱著奇怪的小曲,最終在溪流中溺水而亡。
米萊斯描繪了奧菲莉亞即將沉入水中之前的樣子,她微翕的唇間仍哼唱著歌曲,衣裙和頭髮在水中飄散開來,幾朵鮮花在她手中凋萎。畫面豐富的色彩,以及半沉入水的奇特雕塑般的姿態,吸引著觀眾的目光。
正如珍妮‧斯拉貝特(Janie Slabbert)為「收藏家」(The Collector)撰文所寫:「即使在死亡狀態下,她依然散發著優雅寧靜的氣息;她雙手輕輕向上翻轉,彷彿已接受了自己的結局。」的確,奧菲莉亞張開的手臂,暗示她已準備好迎接即將來臨的死亡。
《沙洛特姑娘》 約翰‧威廉‧沃特豪斯1888年作
在這幅畫中,約翰‧威廉‧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描繪了同代大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爵士(Alfred, Lord Tennyson)作品中的場景。丁尼生深受亞瑟王傳說的啟發,這是「藝術孕育藝術」的另一例:他以詩歌體重述了亞瑟王的傳說,相關作品包括敘事詩集《國王的田園詩》(Idylls of the King)。
一首單獨成篇的詩歌《沙洛特姑娘》(The Lady of Shalott)講述一位女子住在流向卡美洛(Camelot,譯註4)河邊的高塔中。她受詛咒不可直接看向塔外的世界,不然就會死去;她只能透過鏡子觀看大千世界,把自己的所見織入掛毯。然而女子瞥見心上人——圓桌騎士蘭斯洛特後,最終選擇打破魔咒——直視真實世界中的卡美洛,從而註定了自己的死亡。她離開高塔,找到一條小船,順河漂向卡美洛。她在到達之前就死去了。

《沙洛特姑娘》是沃特豪斯最著名的畫作之一,畫中女主人公乘船順流而下,趨近生命的終結。這幅畫既有照片般的逼真,又充滿神秘和幻想氣息,令人歎為觀止。沃特豪斯憑藉綿密而豐富的細節和色彩,將死亡來臨前的一刻生動地呈現出來。
從這位女子的面容中,觀眾可以看出,她知曉自己命已不久;她的表情帶著深沉的哀傷、疲憊與脆弱,但依然保持著平靜。她坐得筆直,一隻手臂微微伸出,目光直視前方,彷彿決意在這世界從她手中溜走之前,盡情地感受它。
正如同沙洛特姑娘透過鏡子看世界,這裏述及的大藝術家們看到了他們嘗試詮釋的神話、詩歌和故事所映出的世界。這些藝術作品故此成為現實的「雙重映射」。文學與藝術的交會更加凸顯了真理與美感,猶如望遠鏡中疊加的透鏡。#
【譯注】
1. 英裔美國詩人奧登(W. H. Auden,1907–1973年)於1938年在布魯塞爾王家藝術博物館觀看了老勃魯蓋爾的一些作品,這些畫作記錄16世紀北歐的民風世俗,也體現了畫家對「苦難」的感慨。奧登由此創作了《藝術宮殿》(Palais des beaux arts)一詩,1940年改標題為「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 Arts)。本文採餘光中譯本。
2. 丹尼爾‧麥克利斯(Daniel Maclise,1806—1870年),愛爾蘭歷史畫家、文學、肖像和插圖畫家。
3. 約翰‧埃弗雷特‧米萊斯(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年),英國畫家,拉斐爾前派三位創始人之一。
4. 在中世紀英國凱爾特民族的亞瑟王傳說中,卡美洛(Camelot)是亞瑟王居住的宮殿、一座金碧輝煌的城堡。#
原文「These 5 Great Paintings Depict Famous Scenes from Literatur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Walker Larson在成為自由撰稿記者和文化評論家之前,曾於威斯康辛州的私立學校教授文學與歷史,他與妻子和女兒居住在該州。拉爾森擁有英國文學和語言學碩士學位,其文章見於《海明威評論》(The Hemingway Review)、「智識外帶」(Intellectual Takeout)以及他自己的Substack(RSS訂閱自媒體平台)「榛果」(The Hazelnut)。他還寫有兩部小說《全息圖》(Hologram)與《球體之歌》(Song of Spheres)。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