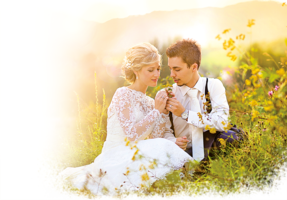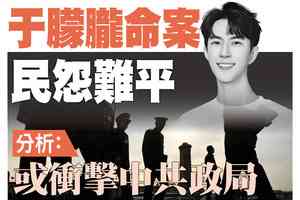最近,我看到一篇幾年前的文章,其中提到一項研究表明,百萬富翁比普通人更加幸福。「哦,不。」我自言自語道,「不會又是那些試圖在財富和幸福之間建立相關性的研究吧。」
顯然,很多人都對金錢是否會增加幸福感這個問題感到好奇。如果不是這樣,經濟學家和其他雜七雜八的文人就不會繼續提出這個問題,並就此發表自己的觀點(是的,只是觀點而已,不是嚴密的結論)。從個人角度來看,我認為經濟學家試圖找到財富與幸福之間聯繫的做法是不公平的、誤導性的,而且有些不太厚道。從經濟學家的專業角度來看,我認為這種研究是徒勞的,因為它們妄圖量化那些無法量化的東西。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裏,經濟學中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甚麼可以量化。許多經濟學家強調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師」(Quants)是對試圖將經濟現象簡化為數字的經濟學家的非正式稱呼。毫無疑問,在某些領域,數據收集和數字計算是合適的。然而,人類生活中還有一些領域是無法量化的,關於這一點我稍後再談。
在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世界經濟思想史。19世紀70年代初,英國的威廉‧斯坦利‧傑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瑞士的萊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等三位著名經濟思想家獨立提出了突破性的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概念。古典經濟學派的主要缺陷在於,儘管它提出了許多有用的見解,但其學者們從未得出令人滿意的價值理論。試想一下,如果對細胞(cell)的理解不正確,生物學將是多麼的歪曲;如果對價(valence)的理解不清晰,化學將是多麼的混亂。邊際論者發現,「價值」(value)並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由個人在特定時間、特定環境下,基於效用和稀缺性,對下一個單位的東西的重視程度決定的;因此,價值不是恆定的,而是波動的。
所謂的「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催生了三個新古典經濟學派。瓦爾拉斯所屬的洛桑學派(the Lausanne school)採用了數學化程度最高的方法論。瓦爾拉斯的繼承者、意大利經濟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提出了人類幸福可以量化的假設。他甚至發明了「util」(幸福值,來自於英文單詞「utility」/效用)一詞,作為他提出的幸福單位。可以想像,帕累托從未成功找到一個普遍接受的「util」定義。我們不可能說,A從某次購物中獲得了10個「util」的幸福,而B從一次相同的購物中只獲得了8個半「util」的幸福。事實證明,現代人試圖量化幸福,並以美元、歐元或日圓的具體數量來衡量幸福,與帕累托量化幸福的努力一樣,遭到了失敗。
除了經濟學家在試圖量化幸福時所面臨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挑戰之外,簡單的觀察和常識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觀的幸福狀態不能等同於客觀的數量,比如一百萬美元。(在此我要順便提一下,作為人類個體的無盡多樣性和獨特性的主觀性(subjectivity),成為奧地利經濟學派(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的一個基本前提。這導致該學派的創始人卡爾‧門格爾提出了主觀價值論(the subjective theory of value),並贊同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好了,廢話少說,讓我們來看看實實在在的人類生活吧。
毫無疑問,我們已經注意到,人類生活是相當複雜的,遠非金錢是幸福的關鍵(或關鍵之一)這種簡單化的觀念所能概括。「金錢帶來幸福」的假設是嚴重的物質主義。它忽略了無形的東西,無論是心理的還是精神的。
我能想像,不少人會反駁以下充滿哲理的觀點:(1)有些人在金錢上很貧窮,但卻相當幸福(無論我們如何定義幸福,即滿足、快樂、開朗、滿意、充實、平靜等);(2)同樣,有些人很富有,但卻很悲慘。
讓我們先來簡單回顧一下第二個觀點。最悲哀的事情莫過於一個人收入豐厚,但卻對自己的工作深惡痛絕,以至於夜夜借酒澆愁。想一想美國詩人埃德溫‧阿靈頓‧羅賓遜(Edwin Arlington Robinson,1869—1935)的黑暗詩歌《理查德‧科里》(Richard Cory,1897)吧,這首詩在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著名民謠搖滾音樂二重唱組合「西蒙和加芬克爾」(Simon & Garfunkel)改編成了一首纏綿悱惻的歌曲。這首詩講述了一個富翁外表風度翩翩、財富顯赫,卻在某個夏夜突然自殺身亡,與仰慕他的貧困市民形成強烈對比。當一些富裕的人找不到幸福時,這樣的悲劇確實會在現實生活中發生。
我認識一些人,對他們來說,財富在許多方面也是一種負擔。有些人花在管理、維護和/或增加財富上的時間比實際享受財富的時間還多。我還認識一些富人,他們焦慮不安,因為他們分不清人們喜歡他們究竟是因為他們的錢還是因為他們自己。
讓人高興的是,關於我所說的一個人可以同時既貧窮又快樂的說法,我可以舉我自己為例。我以優等生的身份畢業,並在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學習了一個學期,之後我決定轉行做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搬到西部,在市內一所高中找到了一份輔導員的工作,專門輔導學區普通高中的輟學生。學期初,歷史老師發現我的歷史知識足以教她的課,便安排我在接下來的三個月裏休假。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數學老師身上。
就這樣,我除了輔導員的工作外,還同時教數學和歷史。我當時的工資並不高,每小時2.10美元,這是當時的聯邦最低工資。我唯一能維持生計的辦法就是打第二份工。我通過照顧一位密歇根州的同鄉獲得了免費食宿,他和我同月大學畢業,卻在畢業五天後的一次工業事故中摔斷了脖子,導致四肢癱瘓。好消息就是,五十多年過去了,這位同鄉還在頑強樂觀地享受著生活。雖然我勉強維持生計,但我還是像以前一樣快樂。然而,市場告訴我,我需要向前看。當時的最低工資和現在一樣,不足以讓我買樓或成家。
讓我還有與我擁有同樣人生觀的很多人如此開心的是,我感覺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在改變一些年輕人的生活。擁有一個有價值的人生目標會提升一個人的幸福感。你認為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快樂僅僅是因為他身價數十億嗎?我認為他很幸福,因為他享受到了自由的恩賜,並利用他的自由去完成極具挑戰性的任務,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如果你知道如何處理大筆金錢,它可以讓你感到滿足,但在許多情況下,完成崇高目標的感覺才會讓人感到更加充實快樂。
我們還可以通過觀察我們身邊的老人,學到關於幸福的寶貴一課。那些快樂的人都找到了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激勵他們每天早上起床,繼續生活。而沒有目標的人往往會陷入沉悶死板、毫無樂趣的生活。巨額存款本身並不能保證幸福。
我甚至還沒有提到我們稱之為「愛」(love)的因素。在人生的不同階段,經濟上勉強度日的人不勝枚舉,但他們卻因為與他人分享愛而深感幸福。相反,也有一些富裕而孤獨的人,他們遠遠談不上幸福。
願你們都能找到給自己帶來幸福的東西。我相信,大多數人都會在金錢買不到的東西那裏找到幸福。
作者簡介:
馬克·亨德里克森(Mark Hendrickson)是一位經濟學家,退休前任職於賓夕凡尼亞州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目前仍然是該校信仰與自由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Faith & Freedom)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研究員。他著述頗豐,研究議題涉及美國經濟史、《聖經》中的無名氏人物、財富不平等問題和氣候變化等。
原文: Are Millionaires Really Happie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新】📊 每周財經解碼
https://tinyurl.com/2asy8m4p
🔑 談股論金
https://tinyurl.com/yc3uda7e
----------------------
【不忘初衷 延續真相】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