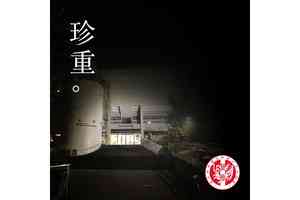2025年10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即將在韓國釜山舉行峰會之際,北京傳出將重新啟動美國農產品採購的消息。中國在2025年9月從美國進口大豆降至零,為2018年11月以來首次出現此情況,但在美中峰會前夕重新下單。市場隨即反應熱烈,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貨價格在消息公布後兩日內上漲約7%-8%,10月單月升幅則超過11%,為近年較強的一次單月漲勢。
對美國而言,大豆出口關乎中西部農民生計與農業票倉政治。根據美國農業部統計,中國市場吸收了美國大豆出口量的約一半,是美國總統選舉中多個「紅州」的重要經濟命脈;對中共而言,糧食進口既是戰略資源,也是談判籌碼。隨著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地緣政治分裂,美中在農產品領域的互動不再只是貿易問題,而是更深層的戰略角力。
從「大豆外交」到貿易戰
中美農產品貿易可追溯至1970年代初。1972年尼克遜(Richard Nixon)訪華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穀物貿易(如小麥、玉米)邁出重要一步。對當時糧食和油料進口需求巨大的中國而言,這代表了其對世界農產品市場初步的對接;對美國農場而言,則埋下了對中農產品出口持續擴大的伏筆。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美農產品貿易迅速擴大。十餘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美國長期處於其主要供應國位置。數據顯示,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大豆出口約3,170萬噸,佔美國該年大豆出口總量的約六成左右。這一時期被視為兩國農產品貿易合作的「黃金期」。
轉折發生在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對中共發動貿易戰,對總值超過 3,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方則以農產品報復,對美國大豆、牛肉、豬肉、小麥、玉米和高粱徵收高達25%的關稅。此舉導致美國對中大豆出口在一年內暴跌逾七成,數百萬噸大豆滯留港口或轉售至其它市場。2018年,中國自美進口大豆不足 1,000萬噸,為十年來最低。
對於美國農民而言,這場貿易衝突帶來了重大挑戰。特朗普政府因中美貿易摩擦緊急推出總額約280億美元的農業救助計劃,以補償農民因中共採購減少與報復性關稅而遭受的損失。儘管此舉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農業選區的不滿情緒,但也顯示出大豆在中美經貿關係中的戰略地位上升,使農業議題正式納入美國對中政策考慮。
2020年1月,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共承諾在兩年內(2020年至2021年)以2017年為基準,新增約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與服務進口。其中,農產品被列為核心項目,象徵雙方嘗試以「購買換緩和」的方式結束貿易戰。
然而,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的追蹤報告,截至協議期滿時,中方僅完成整體採購目標的約58%(涵蓋商品與服務)。若僅以農產品計算,完成度約在77%至83%之間。美國大豆出口在協議簽署後一度反彈,但依據美國農業部與伊利諾大學農經研究(Farmdoc Daily)的分析,出口量與市場份額始終未恢復至2017年的水準。
這一輪反覆上演的「採購–中斷–再採購」循環,讓農產品交易逐漸超越市場邏輯,進入地緣政治的灰色地帶。它不再只是貿易統計表上的一欄數字,而成為一種外交工具——既可作為妥協的象徵,也可被用來施壓,或釋放暫時的善意。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表示,《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實際上是一種「管理貿易」安排——政府以協定方式分配進口配額,取代市場決策。這使得農產品在中美關係中被政治化,成為兩國角力的政策槓桿。多家美國智庫認為,農產品採購在中美關係中被用作一種可量化的政治訊號——用以測試雙邊關係的溫度。
到了2025年,美中再度圍繞農產品展開談判,這場糧食與政治的糾葛,顯然仍未劃上句號。
習特會前後:大豆政治再現
2025年春季,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溫。中共宣布對多項美國農產品加徵10至15個百分點關稅,並以「國家安全」為由強化報關與檢疫審查,實際提高美國出口商的市場門檻。對美國而言,這不僅是又一輪經濟壓力測試,也幾乎宣告了 2020年《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框架的終結。
根據貿易資料監測機構(Trade Data Monitor)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統計,自2025年1月以來,美國對中農產品出口總額下降超過68億美元,跌幅高達73%。在中西部與南部農業州,這一打擊尤其沉重。美國出口商同時面臨一系列非關稅壁壘——從檢疫標準、產地證明到報關程序——使其更難維持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投入成本的上升又進一步壓縮了利潤,使美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喪失部份競爭力。
受衝擊最明顯的是大豆產業。作為美國出口額最高的農產品之一,大豆在2024年的出口值超過240億美元,而中國長期是其最大買家。自2025年4月中共將美國大豆關稅提高至34%後,進口量幾乎降至零。根據CSIS的估算,截至10月,美國對中大豆出口損失已達57億美元,跌幅與2018年貿易戰時期相當。當年中方同樣對美國大豆徵收高額關稅,導致美方出口暴跌。雖然雙方在2018年12月達成臨時和解,但協議生效已晚於收穫季,損失幾乎無法挽回——如今這一幕再度上演。
中共減少對美國大豆依賴的最大受益者是巴西。由於巴西大豆的播種與收穫季與美國相反,中國買家傳統上在上半年採購巴西大豆、下半年購買美國大豆。然而,隨著美中關係再度緊張,中方提前鎖定南美供應。自2025年初以來,巴西大豆月度出口量平均較歷史水準高出約10%,並多次刷新紀錄。阿根廷亦趁勢填補缺口,其1月至8月大豆出口額同比增長超過20%。這場供應重組正在改寫全球糧食貿易版圖,也凸顯地緣政治對農業產業鏈的深層影響。
貿易戰的衝擊不只大豆。2025年3月,中共撤銷數百家美國牛肉加工廠的出口許可,導致對中牛肉出口量暴跌九成,進口缺口迅速由澳洲填補。加州杏仁產業同樣受挫——中共將杏仁關稅提高至45%,迫使美國出口商轉向印度與中東市場。不同於牛肉與大豆,杏仁業早在2018年就推動出口多元化策略,如今雖減少對中共的依賴,但仍難完全抵消市場收縮帶來的衝擊。
這一系列變化,使習特會前後的談判籌碼更為複雜。對美國而言,農產品出口的波動不僅關乎中西部票倉的穩定,也影響白宮的對中政策評估與國內政治壓力;對中共而言,進口結構的調整既是戰略防禦,也是糧食安全政策的延伸。糧食再次成為地緣政治的籌碼,而大豆——這粒看似普通的作物——再度回到外交談判桌的中心。
市場觀察人士認為,從這次特朗普與習近平的會面情況來看,雙方在短期內仍難以完全脫離彼此,但在長期方向上都在積極尋求調整與分散風險。換言之,美中之間的經貿關係正進入一個邊合作、邊脫鉤的過渡階段——雙方都在為自身爭取戰略緩衝期。
農業即政治:美國票倉與外交的共振
農產品在中美政策格局中的角色,一直微妙而關鍵。對美國而言,農業早已不只是經濟議題,而是社會穩定與政治選舉的壓力指標。在美國政治版圖上,「農業帶」(Farm Belt)橫跨愛荷華、內布拉斯加、堪薩斯、伊利諾與印第安納等州——它們既是美國的糧倉,也是共和黨的傳統票倉。這片地區的經濟結構高度依賴農業出口,其政治氣候則與農民收入緊密相連。
當對中貿易順暢時,糧價上漲、農民得以更新設備、償還貸款,地方銀行與零售業隨之活絡;而一旦出口受阻,信貸與消費便會同步收縮。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美國中西部農業州首當其衝。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的報告顯示,該區農業收入在當年明顯下滑,農地價值觸及多年低點,農貸延期與破產申請同步上升。
這些波動不僅反映經濟起伏,更直接傳導至政治層面。對許多地方選民而言,糧價的漲跌與白宮的決策幾乎劃上等號。
這種結構性依賴,使美國農業政策天然帶有政治色彩。歷屆總統皆深知此點——從小布殊時期上千億美元規模的農業補貼,到特朗普時期超過280億美元的貿易補償計劃,皆以經濟援助穩定農業票倉。愛荷華與威斯康辛等中西部州的農村選票在歷屆大選中具有搖擺效應。
對共和黨而言,「賣出一船大豆」有時意味著「贏下一個郡」;而對民主黨而言,如何在關稅、氣候政策與農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則是持續存在的政治難題。
因此,「農業即政治」幾乎成為美國政策運作的潛規則。每當中美重啟農產品磋商,背後不僅是貿易與糧價,更牽動中西部農村的選舉情緒。美國關注出口統計,中共則觀察農民對白宮政策的反應——這場糧食與政治的共振,從未真正停止。
中共的糧食焦慮與戰略部署
對中共而言,農產品從來不是單純的貿易項目,而是政權安全的一環。近年來,隨著地緣政治風險上升與氣候異常頻發,「糧食安全」已被正式納入中共的戰略規劃。自2023年起,官方文件多次強調「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裏」——這句政治口號的背後,是中共對外部供應鏈依賴的深層不安。
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2023年全年進口量接近一億噸,主要用於榨油和飼用,榨油以後的豆粕用作飼料生產原料。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大豆種植與產量增長乏力,而消費需求迅速擴大,進口依賴度長期維持在80%以上。這種結構性依賴使其在貿易摩擦中格外脆弱——每一次中共與美國的關稅對峙,都直接牽動國內糧價與通脹。
為了降低對美依賴,中共近年來在農業領域推動三項並行策略。第一,地理多元化:大幅增加從巴西、阿根廷、俄羅斯與哈薩克等國的大豆與豆粕進口,並支持中資企業在南美建立榨油與倉儲設施。
第二,國內替代化:中共自2018 年起推動大豆振興計劃,以東北主產區為重點,推廣高油高蛋白新品種、恢復部份輪作地塊,並支持「豆粕減量替代」配方研發。
第三,戰略儲備化:2025年起,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將大豆納入戰略儲備範圍,並在年度預算中明確提高相關比重。
在官方論述中,這些措施被視為從「糧食安全」邁向「自主可控」的制度建設。但在實際操作層面,這更像是一種靈活的平衡:既要維持對外進口的多樣性,以分散地緣政治風險,又要防止因突發衝突導致供應中斷。中共在貿易談判中多次以農產品作為槓桿——既能釋放善意,也能施壓——正體現出其對美農產品的結構性依存如何被轉化為策略工具。
到了 2025 年,這種焦慮進一步放大。自春季起,隨著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升溫,巴西與阿根廷雖暫時填補部份缺口,但其物流能力與氣候變數令供應不穩。在此背景下,中共採取了雙向策略:一方面加快全球布局,另一方面強化國內糧食安全宣傳,以政治口號穩定民心。
對外,中共在與俄羅斯、巴西及部份非洲國家的糧食合作項目中推動以人民幣計價或「去美元化」結算;對內,則通過政策文件與宣傳反覆強調糧食自給的戰略意義。這種內外並行的策略,既是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反應,也反映出決策層對糧食問題的深層焦慮。
大豆的角力仍在延續
自1970年代的「黃豆外交」以來,美中農產品貿易的角色早已超越市場範疇,成為雙邊關係的重要風向標。每一次大豆價格的波動、每一項進口政策的調整,背後都傳遞著政治訊號——合作或對抗、緩和或試探。
對美國而言,農產品關乎選票與產業鏈穩定;對中共而言,糧食關乎政權安全與社會穩定。農產品在兩國關係中同時承載經濟與政治涵義——既是談判籌碼,也是戰略資源。
2025年10月的習特會,讓大豆再度成為全球市場的焦點。短期內,雙方仍難以脫離彼此——中國需要進口,美國依賴出口;但從長遠來看,雙方又都在為可控的脫鉤爭取時間。#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