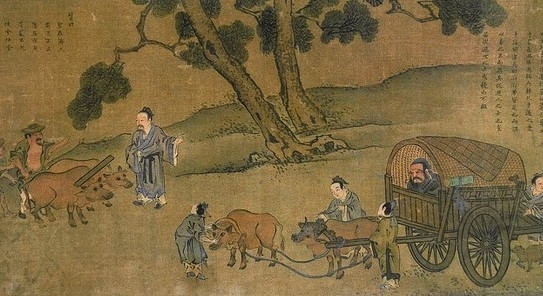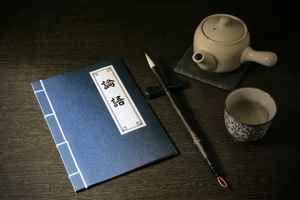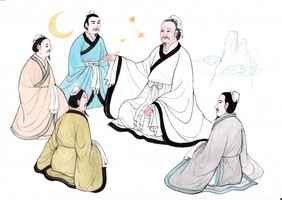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七》)
【註釋】
桴:音fú,古代把竹子或者木頭編成簰,以當船用,大的叫筏,小的叫桴。
從:動詞,舊讀去聲,跟隨。
材:可解做木材。或說同「哉」,古字有時通用。或說與「裁」同,古字借用(朱熹)。
【討論】
本章頗有名,但解讀分歧大。孔子說:吾道是不能行的了。我想乘木筏漂浮到海外去,估算只子路一人會和我同行吧!子路聽了大喜。孔子又說,由呀!你真好勇過我,卻無所取材。
關於「無所取材」,第一種是詼諧理解,「可惜我們找不到造筏用的材料啊!」《論語註疏》中說:「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
在此,孔子對子路有所批評。為甚麼呢?張居正解讀:凡人懦弱者,多憚於涉險,子路不以浮海為懼,而以得從為喜,這等好勇豈不勝人乎!然海豈可居之處,孔子豈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子路遽以為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宜矣。
錢穆說:此章辭旨深隱,寄慨甚遙。戲笑婉轉,極文章之妙趣。兩千五百年前聖門師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論語》中別成一格調,讀者當視作一首散文詩玩味之。又說:義理、考據、辭章,得其一,喪其二,不得謂能讀書。
第二種,理解為嚴辭批評,「子路啊我對你無所取用」,「子路沒有甚麼可取的呀」。《論語》中孔子批評子路處甚多,有時還相當激烈。但孔子的教學藝術恰到好處、高明入神,不會總是一副面孔;而從本章文意體會,更應是委婉教導。再聯繫本章的前後,若理解為嚴辭批評,則顯得突兀。
大家知道,孔子是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孔子其實知道吾道不行,但仍周遊列國,為甚麼?因為要在人間留下道。中國行不通,就上海外去,只要有簡單的桴,一切危險也都不顧,以道為重。於此,《論語‧子罕》中還有一處記載可相印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從這個角度講,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顯得多麼英勇豪邁、一往無前、決絕悲壯!可見聖人雖有傷時之意,而終無忘世之心。
不過,有多少弟子能隨孔子「乘桴浮於海」呢?可能孔子也不樂觀,所以接著說了句「從我者其由與?」這對子路又是多高的肯定和評價啊!
但是,子路雖然勇於為義、臨難不避,非常難得,卻於「道學問」有不足(《論語‧先進》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因此,本章孔子在激賞子路之餘,又指點他「好勇過我」(孔子「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鞭策他提升學問修養。#
主要參考資料:
《論語註疏》(十三經註疏標點本,李學勤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論語集注》(朱熹,載入《四書章句集注》)
《四書直解》(張居正,九州出版社)
《論語正義》(清 劉寶楠著)
《論語新解》(錢穆著,三聯書店)
《論語譯注》(楊伯峻著,中華書局)
《論語今注今譯》(毛子水注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論語三百講》(傅佩榮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論語譯注》(金良年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論語本解(修訂版)》(孫欽善著,三聯書店
《論語今讀》(李澤厚著,中華書局,2015)
看更多【論語說】系列文章。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