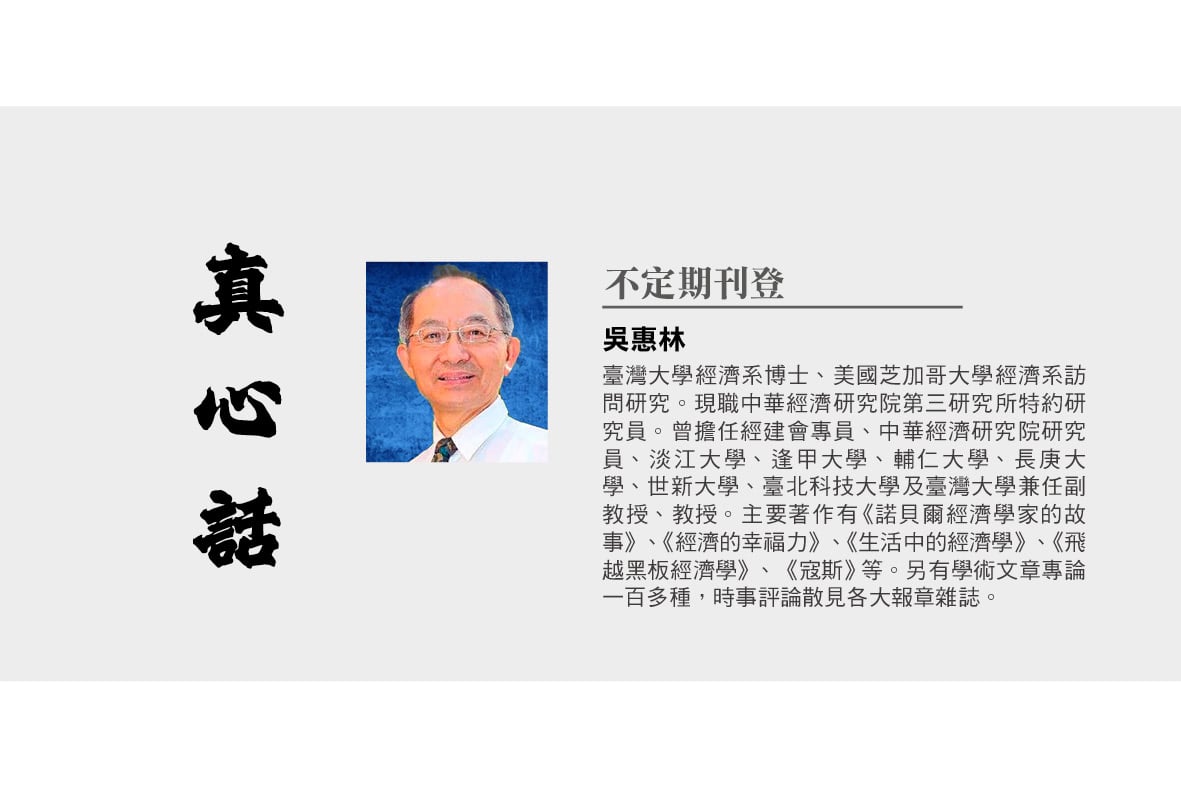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三位對『創新』研究有貢獻的學者,可見『創新』的重要性。這也讓我想起一九九九年四月, 被台灣媒體封為「競爭力大師」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 再一次抵台發表「高價」演講。儘管被形容「價碼高」,但以座無虛席的場景言,可推知向隅者應不少 ,如此,相對來說,其票價實際上是「便宜」的。真實的市場景況是如此這般, 只不過聽講者「事後」是否都覺得「值回票價」呢?這都藏在聽講者的個人心中無法客觀得知, 但由媒體報道及有些評論,可知波特此行似乎並不像上次帶來「鑽石理論」算是有創見,而只提出 「創新」這個老掉牙的創意名詞。不過,由今日諾貝爾獎再度肯定,可知「創新」的歷久彌新、顛撲不破,甚至愈陳愈香。那麼,「創新」的原創者何許人也,它又是何義?
「創新」理論溯自一九一二年
「創新」(innovation)這個名詞的出現,可追溯到一九一二年,在《經濟發展理論》(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這本名著中出現,其作者是鼎鼎大名、已故的奧國學派一代宗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雖然熊彼得普遍被歸在奧國學派行列,但其一些主張其實與奧國學派的傳統差異極大, 尤其一九三三年赴美國哈佛大學任教,歸化美國之後更是,例如他大力提倡的經濟學數理化,就是奧國學派抵死反對的。在二〇〇〇年時,熊彼得還被路透社一項對經濟學者調查 「過去這幾個世紀以來,誰最具經濟影響力?」,選為第五名,次於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馬克思(Karl Marx)和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可見其影響既深且遠。
熊彼得提出「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這種主張,他所謂的「創新」其實就是將各種生產要素加以「新的組合」,以當前流行的經濟學術語,就是「不同的生產函數」。所以,所謂的「創新」也就是創造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使各個生產因素在不同組合下,能創造出更多的產出。由於在任何一個時期內,生產函數都可以表示為依社會在當時的知識水準下,每一生產單位所能使用的技術,因而「創新」往往與「技術進步」同義。
具體而言,「創新」概念包含五種:一是新物品的提出,或對一件原物在性質上作某種改進;二是新生產方法的提出;三是新市場的開發;四是新原料或半製成品來源的發現;五是新產業組織的形成。
對照熊彼得一九一二年的說法,波特和當時台灣枱面上與之對談的成功企業家有沒有 「創新觀點」?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的談話內容不重要,也不是說創新沒價值。反之,我們可以明顯得知,熊彼得早就道盡現代社會如何前進的秘訣,在歷經一百多年還能閃閃發光,足見這個理念禁得起考驗,是顛撲不破的。二十世紀末二〇〇〇年千禧年,新經濟、知識經濟響徹雲霄,但就其本質內涵,仍然脫離不了創新這個老概念。
歷久彌新的「創新」說
其實,不用波特等人再炒這個觀念,一般的中外標準教科書中, 已白紙黑字將擔任創新角色託付在「企業家」身上。翻開任何一本中外經濟學教科書,都會告訴我們生產要素可歸為四種,一是勞動;二是資本;三是土地等自然資源;四是企業精神。最後一種就是所謂的「企業家」所擁有的特質。一個基本的問題是,勞動和企業家指涉的對象既然都是「人」,為何需要作這樣兩種不同生產要素的區分呢?若作深一層的探索,其中的確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不過,如果予以簡單化,是可以作這樣的區別:勞動指的是有形的、可以量化的勞動數量及其提供的勞務, 通常以「人數」或「工時」作為單位,其單位價格或報酬常以「薪資率」或「工資率」稱之;至於企業精神的解釋就比較棘手,較為通用的解釋就是熊彼得提出的創新行為,值得一提的是,必須對「創新」(innovation)和「發明」(invention)作明確區分,前者是發明之中具市場價值者才算,而後者可用「無中生有」稱之,此與當前的「研究與發展」(R&D)這個通用詞差可看成是同義詞。
由於發明原本就不簡單,既勞心又勞力,又得耗費其他的成本,進一步要得到市場人士的青睞當然更艱鉅了,因其必須冒著偌大「風險」,以及具備對抗「不確定性」的勇氣和擔當,血本無歸的機率是難以估量的,一旦成功當然也應當有較高的利得。,就因為需要具冒風險的無比勇氣,並且也要擁有較高的能力,一般凡夫俗子似乎被認為較難做到。即使有勇氣冒險,也有發明的熱忱,但卻屢試屢敗,這種人當然無法列入企業家,也不能稱其擁有企業精神。準此,標準經濟學教本裏,就將企業家的報酬特別再以「利潤」稱之,意義是「總收入減去總成本」,其有「剩餘」、「加值」之內涵。當然,我們所說的成本都是「機會成本」,這裏所說的利潤指的是「經濟利潤」或「超額利潤」,是超過「正常利潤」的那一部份(對這些基本名詞不了解的讀者,可以查閱任何一本當代經濟學教科書)。
人人都可以是企業家
經由這樣的解析,我們其實可回歸到一個非常簡單的、但也可能讓大多數人費解的觀念,此即有能力創造多餘利潤者就是具企業精神的企業家,如此,不必是大公司的負責人、 不必是社會名流,都可以是企業家。換句話說,能創造「多餘價值」者就是企業家,所以, 全人類的企業家似乎比比皆是,差別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但,我們必須再加上「不以暴力 、欺騙、脅迫手段」、或「以光明磊落、誠信倫理態度來創造利潤者」就是企業家,其精神就是企業精神。這種認知與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就說出的「企業家只有一個責任,就是在符合遊戲規則下,運用生產資源從事提高利潤的活動,亦即,需從事公開和自由的競爭,不能有欺瞞和詐欺。」不是大同小異嗎?而將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作這樣的引伸,是否與熊彼得的原意不符,這有賴讀者們仔細研讀這本《經濟發展理論》。
讀這本一九一二年的舊作(英譯本一九三四年),再對照今日的經濟學書籍,不免有所感觸 ,今天的經濟學家,雖然也強調「人的行為」,但其實在圖形和數學模式的包裝下,幾乎與 「機械人」無異,完全失去了人味,而讀熊彼得的書,就覺得有人的呼吸在,特別其強調經濟制度內在因素,更是當前經濟學書籍所丟棄,但卻是極其重要的。因此,很高興能看到本經典書中譯在台灣出現,可是由於本譯本出自中國大陸學者,一些用語會讓台灣讀者多費一番思量,即使如此,其精髓仍然存在呢!雖經近四年後才再版,但在此速食化、不重視讀書的時代,這麼生硬且不易懂的翻譯書得以再版,更證明其具長遠價值性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