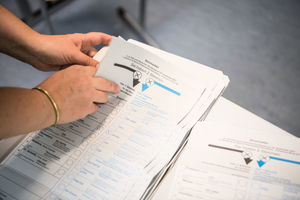2025 年10 月25 日中午,德國巴伐利亞州貢德雷明根核電站(Kernkraftwerk Gundremmingen)兩座160米高的冷卻塔被受控爆破拆除。爆破使用了約 600 公斤炸藥 和 1,800 個鑽孔,共破碎約 56,000 噸混凝土結構。該操作是德國核電退役戰略的一部份,是德國徹底棄核的象徵。該核電站的最後一個反應堆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就已經停止運作。
選擇黨主席魏德爾(Alice Weidel)女士抨擊說,這是對能源基礎設施的肆意破壞。她的話既引發爭議,也引起共鳴。但共鳴和反對的聲音來自德國社會中截然不同的群體,立場看法差異很大。
魏德爾把「核電退役」重新命名為「故意破壞」,暗示政府在主動損害國家利益,形成情緒動員,而不是技術討論。她的話本身不是討論工程與安全問題,而是對政府的能源路線進行價值判斷和政治指責。不過,其言論確實抓住了「高電價 + 工業焦慮 + 能源安全」這三個德國現實痛點。
誰會產生共鳴?首先是製造業企業主和工程師,感到電價太高,直接影響產品競爭力。德國工業電價為歐洲最高之一,大約 0.18 USD/kWh。而美國約 0.08 USD/kWh,中國約0.088 USD/kWh。其次是巴伐利亞、薩克森等南德傳統工業區民眾,擔憂能源安全,俄烏戰爭引起天然氣供應危機後,不信任風光電能穩定供電。第三是對綠黨能源政策不信任者,認為綠黨理想化,脫離實際,棄核太快,轉型太急。
誰反對?首先是綠黨及其支持者,認為退核是民主共識、法律決議,必須執行,因為核風險和核廢料的長期性,應當優先考慮可再生能源。其次是環保組織,認為核廢料無最終解決方案,強調跨世紀的代際責任。還有一些自由派知識群體,擔心「選擇黨利用恐懼情緒分化社會」,指責魏德爾的表述是政治煽動。他們的核心立場是:核電不是技術問題,是風險倫理問題。
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女士是量子化學博士,有完整的物理學和科研背景。她原本是支持核電的,認為核電可以為德國提供穩定的低碳基荷電力。在她執政的早期(2009 年左右)甚至延長了核電站的運行壽命( 8~14 年)。但 2011 年3月福島核事故改變了她的決策。
眾所周知,福島事故不是技術故障本身,而是地震加海嘯,再加上失去冷卻功能的複合災難。對於德國社會來說,關鍵不在事故細節,而是「即使技術很成熟,只要有萬分之一的極端情況,後果仍不可承受。」這觸發了德國社會內部長期存在的反核文化記憶。德國幾十年反核運動的社會基礎很強,早在 1970–1980 年代就有環保運動、反核示威、宗教和平主義潮流,而且與民主進程綁定。1980年,反核運動直接促成了德國綠黨(Die Grünen)的誕生。德國的反核不是臨時情緒,而是深層文化結構。在許多德國民眾心中,反核抗爭 = 反威權、反國家機器、反軍事、反污染 、捍衛民主與環境。其原因來自德國歷史:(1)納粹時代國家極權製造災難,導致德國社會形成對強力國家技術體系的極不信任;(2)冷戰鐵幕邊界和核威懾環境,導致核武器與核能在集體記憶中是「毀滅力量」。
這個社會背景同日本和法國差異很大。法國民眾普遍相信國家工程體系,甚至認為核電是國家榮耀與獨立象徵(戴高樂傳統);日本有服從文化根基並信任技術官僚體系,雖遭受過原子彈攻擊和福島核災難,但認為核電是能源生存必需品,所以態度矛盾,既恐懼又依賴。
默克爾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政治家。她不是「害怕核能」,而是看準了民意,判斷德國社會無法接受繼續運行核電站的政治風險。為了避免國家陷入長期政治對立與社會撕裂,她宣布:加速關閉核電站。2023 年 4 月,德國徹底結束民用核電。
我從自己的核專業角度是不贊同德國的棄核政策的。但我也看到德國強大的反核勢力,所以對默克爾的決策表示理解。
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在能源體系尚未完全轉型成功之前,過早廢除核電對德國經濟的發展沒有好處。風光電波動性高,需要大規模儲能和調峰,而且成本偏高。沒有強大的基荷電力,電網是不穩定的。
德國徹底退出核電之後,從法國、比利時、荷蘭和捷克等鄰國大量進口電力,其中相當一部份是核電。這可不是政治口水,而是實實在在的電網與能源流向數據。當風不吹、天不亮,德國就需要從鄰國調電。這在我看來,相當滑稽可笑。如果鄰國的核電站發生重大事故,德國也可能遭受重大影響呀。德國的核廢料儲放在邊境地區,鄰國的核廢料可能也放在邊境地帶呀!德國的不同陣營對此看法多極化。綠黨及支持者認為,「核電是不可承受風險,進口是過渡,不是依賴。」工業界與選民中務實派認為,「自己拆核電,卻花更多錢買別人核電,這不理性。」選擇黨(AfD)等反對黨認為,這是執政黨「能源政策失敗」的證據。
1982年在清華大學畢業時,我在班教室黑板上寫過一首打油詩:「頭裝原子彈,心繫中子線。立足反應堆,放眼核電站。」對核專業充滿信心。接著,我參與了中國核工業部同美國的合作項目——核電安全分析程序Relep5的開發應用。隨後,我參加過核電站安全殼的設計工作,現役核潛艇的安全分析和新型核潛艇的研究設計等。1987年我到慕尼黑理工大學學習,後來在德國反應堆安全協會工作。我在德國從事了一系列關於核反應堆安全的實驗分析、程序發展和驗證等工作。古稀之年,看到德國徹底放棄核能,感慨萬千!
38年前,我剛到德國不久,就見證了德國強大的反核勢力。我讀過他們的許多反核宣傳資料。對我這樣的核專業人員來說,他們的宣傳小兒科居多。他們中一些人把核電站等同於原子彈,讓人哭笑不得。他們到核電站抗議,阻止運送核廢料的列車通行等等。他們甚至包圍了慕尼黑加興研究中心 (Garching Forschungszentrum)的核研究反應堆進行抗議。我同他們有過一些面對面的辯論。我說,反應堆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堆芯燒燬放射性洩漏的危害很大,但發生重大事故的概率非常微小。核廢料處理的最大困難只是高放廢料(乏燃料)的儲存,但不到全部核廢料的1%。深地質處置可以把風險降到很低。核電穩定可靠、價格低廉,在正常運行時對環境的影響很小。煤電、油電、氣電對環境的影響大得多,會產生溫室效應,破壞地球生態。我們不能因為有車禍、空難、沉船,就拋棄汽車、火車、飛機和輪船等交通工具。而且,迄今為止的礦難,超過核災難千百倍。當然,他們說服不了我,我也說服不了他們。
能源倫理與現實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引起激烈爭議。說到底,這不是電力問題,是價值觀和國家路線衝突。不管怎樣,因電價高漲,企業成本增加,利潤降低,競爭力減弱,部份德國製造業出現外遷趨勢,去美國、東歐甚至中國,這對德國是極為不利的。
我認為,宇宙的初始能源是核能,人類的終極能源也是核能。隨著高溫氣冷堆(具備不熔芯的固有安全機制,熱效率高、可用於制氫和工業用熱、並可模塊化和小型化),快中子增值堆(將鈾資源的利用率從不到1% 提高到 50–70%),釷基反應堆(釷的儲量是鈾的3-4倍、廢料半衰期更短)、聚變反應堆(燃料取之不盡,不熔芯、廢料少且半衰期短)等第4代、第5代和第6代核反應堆的研究發展商用,德國也會重啟核能。#
2025年11月1日 寫於 紐倫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