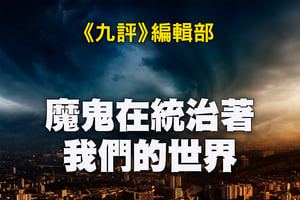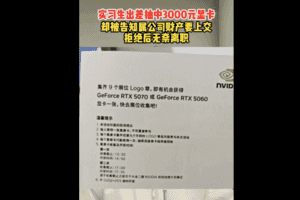將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作為政策指導的支持者,尤其在聰明人比比皆是的大學裏面的支持者,最讓我感到驚訝的一點就是,積極、主動的歧視(這是DEI政策的必然結果)會帶來消極、被動的歧視。畢竟,人們在偏袒某些人而進行歧視的時候,不可避免構成了對其他人不利的歧視。
這並不是一個很難理解的想法,相反,它的邏輯是顯而易見的。那麼問題就來了:為甚麼許多人在聲稱他們因任何形式的歧視而感到被冒犯的時候,似乎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呢?
有時,在反駁一項你不同意的政策時,最好先想出對它最好的評價。就DEI政策而言,我們可以進行以下深入的分析。
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裏,有些年輕人一開始就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優勢,而處於不利地位的年輕人往往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些公認的社會群體。如果來自這樣一個群體的年輕人在學校表現出色,儘管不如來自更有優勢群體的人,我們有理由認為他不僅和優勢群體的人一樣有能力,而且在克服自己的劣勢方面表現出了更大的勇氣。因此,在有限名額的競爭中,他將成為優先考慮的候選人,而且,在優先考慮他而不是更有優勢的候選人時,他所來自的弱勢群體將得到幫助,從而與更有優勢的群體平起平坐。
這一切的理論依據是一種簡單甚至粗糙的歷史、社會和人類心理學理論,然而這種理論卻具有某種蠱惑人心的吸引力。然而,它最吸引的正是某個日益壯大的階層,即行政官僚階層。它賦予了這個階級一種權利和義務,可以制定和強加無窮無盡的行政程序。
正如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常說的那樣,這個政策即使不是蘇維埃發明的,也是蘇維埃沿用的,這絕非巧合。「正確的」(correct)社會背景,也就是無產階級或農民身份,成為進入高等學府的必要條件,再加上這個群體人數的大幅增加和意識形態的嚴格統一,很快就導致了質量的急劇下降。只有那些直接應用於武器裝備開發的研究,才會在遴選時嚴格考察過硬的專業能力和個人成就。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考慮只是出於社會工程,更準確地說,是政治工程。
最近,我正好在讀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1869-1951)撰寫的兩本關於20世紀30年代時期蘇聯政權的書,這兩本書分別是《從蘇聯歸來》(Return From The USSR, 1936)和《我從蘇聯歸來‧修訂本》(Revisions to My Return from the USSR, 1937)。
紀德和大多數法國知識份子一樣,是蘇聯政權的支持者,幾乎可以說是不假思索的支持者。然而,儘管他在1936年去蘇聯時受到了王室般的待遇,他回國後卻成為了一名蘇聯的批評者,尤其是對蘇聯缺乏知識自由的批評。他的第一本書在當時受到其他作家和知識份子的嚴厲批評,幾乎被視為背叛事業的行為。對此,在對蘇聯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後,他在第二本書中做出了回應,對蘇聯進行了更為嚴厲和準確的批評。
他對蘇聯官僚機構的描述在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引人關注,因為官僚機構在大學(但不僅限於大學)中發展得十分龐大,甚至十分怪異。下面是紀德寫的:
「有人說,史太林本人已經成為這個官僚機構的奴隸,這個官僚機構最初是為了管理,後來是為了統治。最難擺脫的莫過於虛職,或者說莫過於毫無個人價值的無用之人。早在1929年,奧爾忠尼啟則(Ordzhonikidze,蘇聯著名政治家、史太林的老朋友,和史太林一樣是格魯吉亞人,在紀德第二本書出版的那一年被謀殺或自殺)就對這種『大量的無用之人』感到震驚,他們對真正的社會主義一無所知,只想阻止社會主義取得成功。奧爾忠尼啟則認為:『那些不知道該做甚麼、沒有人需要的人被安排到了行政部門。但是,他們越是無能,史太林就越能指望他們的唯命是從;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好日子完全歸功於史太林的恩寵。不言而喻,他們是政權的熱情支持者。在為史太林的好日子服務的同時,他們也在為自己的好日子服務。』」
如果我們把「那些對真正的社會主義一無所知、只為阻止社會主義成功而工作的人」換成「那些對學術獨立一無所知、只為阻止學術獨立實施而工作的人」,把史太林換成大學校長或校董,這個類比就非常接近了。
1936年,蘇聯的《真理報》(Pravda)本身對蘇聯制度的批評並不嚴厲,但它間接提到了這樣一個事實:機械化農場裏14%的僱員是官僚(工資比農場工人高)。按照現代美國大學的標準,這種效率令人吃驚。例如,史丹福大學(Stanford)有17,529名學生,但有18,369名行政人員,平均每8名行政人員對應1名教職員工。奧爾忠尼啟則會在墳墓裏氣憤得翻身,但史太林卻會高興得大笑。奧爾忠尼啟則始終認為西方註定要滅亡,這就是證據。
目前大學出現的問題也普遍存在於其它機構,雖然問題最為嚴重的還是那些州立或公立大學。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好逸惡勞者個人都是不誠實的。要知道,人的大腦能夠說服自己相信任何事情,然後忘記曾經需要這種說服。我曾親耳聽過一些高級官員說,他們熱衷於某個部門這樣或那樣的功能,然而僅僅過了一周,他們又以同樣的信念論證說,必須立即關閉該部門。他們的理智信念源於他們從高層接到並必須執行的命令,他們在執行命令時會立即將其合理化,這樣他們就不必為自己感到難過。
從這個意義上看,有些人與其說是理性動物(the rational animal),不如說是合理化動物(the rationalizing animal)。#
作者簡介:西奧多‧達林普爾(Theodore Dalrymple)是一名退休醫生,他是《紐約城市雜誌》(City Journal of New York)的特約編輯,著有《生活在底層》(Life at the Bottom, 2003)等30本書。其中最新的一本著作是《禁運和其它故事》(Embargo and Other Stories, 2020)。
原文: Discrimination by Design: The DEI Logic No One Wants to Fac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