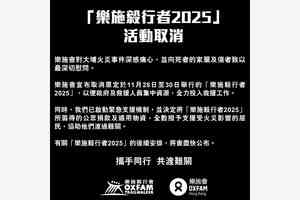我是吃麻辣火鍋長大的小孩。
每逢家庭聚會、每逢家裏大人談生意或公司聚會,我總是被大人帶去吃火鍋。小小的我已經養成了吃辣的能力。大人們都在努力社交,談笑風生中大吃特吃,我總是點到為止,就和其他小孩結伴出去玩了。對於小孩子來說,玩總是比吃更重要。
川渝火鍋的湯底用料也很豐富,基本分為清爽清油鍋和熱情牛油鍋,重慶火鍋用牛油炒鍋底,吃起來味道雄渾醇厚;成都火鍋則用菜籽油炒鍋底,吃起來細膩柔和。食材亦豐富,毛肚、鴨血、肥牛、黃喉,以及各種素菜……
在我的世界觀還很小,沒有超越家鄉時,我以為全世界的人都要吃麻辣火鍋。長大一點才發現,哦,原來只是我的家鄉才這麼愛吃辣。
不過在冬至那天,畢竟「冬至如大年」,我們家鄉一定會吃羊肉火鍋,喝清香濃郁的羊肉湯,調味料可以加辣。我最愛的環節,是吃羊肉吃得心滿意足的時候,開始煮豌豆尖。
你知道嗎?這個豌豆尖作為雲貴川特有食材,清香味甘,是豌豆幼苗頂端最鮮嫩的芽葉部份。每年11月上市,最佳食用期只有一個月!
冬天外面天氣那麼冷,我們在室內吃著羊肉鍋卻非常溫暖。後來去了海外,我就再也沒有在冬至節喝到羊肉湯了。
喝羊肉湯的童年當下,我自然是懂不了,人生其實是有期限的,能和家人完整相聚的時光,其實也是有quota(限額)的。那些年一起喝羊肉湯的親人,有的已經消逝了,一場地震,一場疾病,但你們還來不及說再見。而人生列車到站了,你就要一個人前往下一站了。第一次離家的小孩,記得學會面對離別,無奈地擦乾撕心裂肺的眼淚吧!
聞香識辣鍋
儘管愛吃辣,我絕不是一位「無辣不歡」的人,往往喜歡入鄉隨俗,到了新地方就開始探索新美食。我認為人總要成長,絕不能老惦記著家鄉美食。
我在香港生活幾年,沒怎麼吃到正宗四川火鍋,忙碌的生活中我也沒有特意去尋找。然而有一天夜晚,我隨意在路上亂走,一股熟悉的麻辣香撲鼻而來,跟家鄉的一模一樣。但是我沒有看見招牌,於是就順著味道一路追尋,終於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看見了一家小小的、裝修普通的火鍋店,由一位移民香港的重慶阿姨開的,她說麻辣湯底都是她自己熬出來的。
那真是一個無意「尋味」的過程,找到後是非常欣喜的。後來在網上搜尋,發現有懂吃辣的香港美食作家,專門寫文推薦了這家店。
記得之前在外地生活了一段時間,坐飛機到重慶機場時,下飛機剛走到飛機場裏的室內商家附近後,麻辣味一瞬間撲鼻而來,毫不誇張。我當時感嘆,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就是這個味兒了。
麻辣火鍋流行在海外
廣東人喝早茶社交、談生意,川渝人則以吃火鍋的方式社交。如今這兩種飲食文化,火遍中國大陸大江南北,也火到海外。以前廣東人移民海外比較多,所以粵菜在海外最常見吧,但現在川菜的勢頭越來越強勢了。
我雖然沒有到處去試吃,但印象裏台灣比較難吃到正宗的麻辣味,這裏食物的味道似乎普遍要甜一點。儘管1949年國民黨撤退台灣以後,川菜也跟著川人逃難到了台灣,但可能時間太久遠,味道的傳承已慢慢消散,當地也漸漸也沒了市場。再或者這只是我的偏見,我只是沒有遇到麻辣的,並不是這裏沒有。
我第一次到台灣時,剛到第二天,遇到一個熱情溫暖的台灣老爺爺,他的眼睛笑成了月牙,他知道我的家鄉後,大聲說:「天府之國,魚米之鄉,我太太愛吃麻辣香鍋!」
香港呢?香港還是能找到一些比較正宗一些的川菜館,但味道還是欠了一些,有些本地化。我覺得這和近年來大量陸人移民到香港有關,而現在的香港年輕人也越來越能吃辣。在香港的四川冒菜館,能見到好多香港年輕人。
紐約就非常厲害了,匯聚世界美食。在紐約曼哈頓這個國際都市,能找到很正宗的川菜館;紐約法拉盛的四川火鍋就非常地道,因為這裏有大量的大陸移民,就有商業市場吧。
錯過的潮汕之行
去的地方愈多,我也開始欣賞廣東的牛肉火鍋。廣東潮汕的牛肉火鍋堪稱一絕,主流的鍋底有清水和牛骨清湯。尤其是清水牛肉火鍋,據說就只是用清水,有時會放幾塊白蘿蔔,加上最新鮮的牛肉。
我在廣州吃了好幾次牛肉火鍋,但潮汕朋友總是自豪家鄉的招牌,她反覆強調:「牛肉火鍋只要離開了潮汕,都不正宗。」
因為正宗的潮汕牛肉火鍋,最講究牛肉的新鮮度。從宰牛,到運送至火鍋店,最後送上桌食用,時間都要控制在6小時內,這樣的牛肉才最新鮮。
大學畢業那年,兩個好朋友力邀我去汕頭遊玩幾日,其中一位還是本地人,她興奮地要帶我們去吃當地最地道的牛肉火鍋。然而,那幾日我不知怎麼突然變得勤奮,覺得不能荒廢時光,便婉拒了邀請。
哪知,人生的太多相遇只是「一期一會」,我再也沒有機會和那兩位朋友一起旅行,連見面都幾乎沒有機會,她們的結婚生子過程我都錯過了,現在想想覺得很是遺憾。
「冬天就是要吃壽喜燒啊」
第一次吃日本的壽喜燒,是在有好多日本美食的台灣。剛在滾水裏煮熟的牛肉沾生雞蛋液,蛋液也沒有那麼生了,感覺牛肉配蛋液是那麼清爽可口。在日本動畫《蠟筆小新》裏,時不時上演吃壽喜燒的情節。印象裏有一句台詞:「冬天就是要吃壽喜燒啊。」一種愜意人生態度,藏在日常美食中。
壽喜燒是日本傳統家人團聚時,最具代表性的家鄉料理。道地的壽喜燒,食用時不加水,僅透過洋蔥、大白菜及豆腐等天然食材釋放出的水份,與牛肉、壽喜燒醬慢火熬煮。在冬日,靜靜吃著壽喜燒,尤其溫暖。
在台灣夜市,我還吃到了一種特色臭臭鍋。臭臭鍋通常指鍋中有臭豆腐的火鍋,而且會由店家烹煮完成後再提供給客人。臭臭鍋和臭豆腐一個道理,聞著臭,吃起來卻很香。這是一種西方人不能理解的「東方特色」。
在紐約聽說有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集市上有中國人做了臭豆腐售賣,結果西方人聞到臭豆腐後,基本都被熏走了,鬧了一個大笑話。
曼谷大雨下的鄉愁
我還對成都的泰式火鍋印象深刻,不知是否在成都的原因,味道可能已經被當地有所同化,但那個冬陰功湯底的味道一直在我的記憶裏,蝦的甘甜至今難忘。
反而我後來去了泰國旅行,卻沒有吃到泰式火鍋。不過在曼谷,看到街上有好多相信是中國人開的四川或重慶火鍋,驚訝的同時,也覺得親切,也很感嘆泰國人對川味麻辣的熱愛,我像是到了第二個味蕾故鄉,在這裏絕對不會餓著。
我也感嘆,這真的是一個離散的時代。新聞說很多中國人受不了中國的「卷」和當年的疫情管控,他們離開家鄉,到曼谷、到清邁,尋找一種壓力不大的新生活。也許他們中就有人就把餐廳開到了泰國吧!
在泰國旅行的十幾天,我和同伴每天享受著泰國菜,如冬陰功、便宜的海鮮大餐、芒果飯。但在泰國最後幾天,我們在曼谷剛好遇到中秋節,那天我們突然對泰國菜就完全不行了,真的就「好想好想吃中餐」。
曼谷有好多麻辣旋轉火鍋店,我們去的那家店面雖然小小的,但是五顏六色的各種食材被放在一個個小盤子裏,不停地在旋轉的餐桌上打轉轉。每個人有一個鍋,煮鍋熱氣騰騰地冒著煙兒,非常誘人。
然而,美食就在眼前,卻可望而不可即——因為這家店只收現金,我們身上沒有泰銖了,需要趕緊去兌換店換取泰銖。9月的泰國還處在雨季,空氣裏都一股熱氣。曼谷的雨像一個急性子的女孩,說來就來,我和同伴也沒有帶傘。於是我們淋著大雨,在曼谷大街上奔跑著衝進了兌換店,成功換到泰銖後,又在雨中衝進了那家旋轉火鍋。
那種滋味非常深刻。為甚麼深刻呢?因為你沒有現金,無法馬上吃到。因為曼谷突如其來的大雨,溫暖潮濕的街上熙熙攘攘,雨聲人聲交錯,我們被淋得濕濕的,再衝進火鍋店,感受那一刻店裏的熱氣騰騰。
我的同伴餓壞了,不說話一直狼吞虎嚥,平時每次都是「手機先吃」的她早已忘記拍照了。
還因為,我們都是無法回故鄉的人啊,一個中秋節的下雨天,在異國他鄉,吃到家鄉美食,那心中自然有很多別樣的深情。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