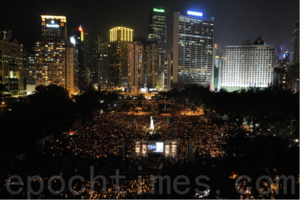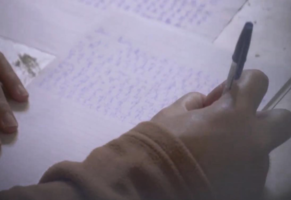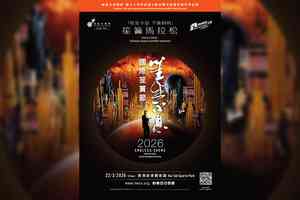天水圍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近日宣布,本學年起取消中英文默書,改用遊戲、AI等方法讓學生識字。校長稱,教學策略應該多元化,例如用AI作曲,學生預習後聽歌填詞,比傳統默書有趣,有助加深記憶。網上對此反應不一:有人覺得默書無用,早就應該廢除;有人擔心不用默書,學生更缺乏動力學習寫字。我自己則認為默不默書並非重點,重點是怎麼默。
默書是什麼?傳統來說,就是老師朗讀文字,學生要盡力一字不差地寫下來,事後對照原文,改正錯處。這樣的學習方式可追溯到中世紀,甚至於古羅馬。但最早期的默書並非為了評估,只因為當時未有印刷術,書本難得,學生只好聽先生口授,自己動手筆錄。到了19世紀,西方教育漸漸普及,默書才成了語文教學及評估的標準工具。
以19世紀中葉的法國為例,默書(la dictée)是小學畢業證書的核心評核元素。自1880年起,當局規定默書若有五處錯誤,就判定為不及格。可見當時法國小學畢業的要求甚高,一張「沙紙」在手,已是就業升職的通行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默書也逐漸成為全球普及教育的核心評核方法。
如今百多年過去,儘管有AI工具輔助,但人類所謂「識字」的標準並無改變:中文字要寫得出,洋文要串得對,抄寫、記憶依然是必需的。問題是:傳統默書是否最有效的學習方法?其實默書的形式,早就不限於「老師朗讀,學生抄寫」這麼死板了。梁銶琚學校使用的「遊戲」學習是什麼,我不太了解,但聽聞英、法等地的新派默書法,行之多年,都比傳統默書更有效——即更能減少學生的聽寫錯誤。
法國有種「協商式默書(la dictée négociée)」,分為三步:第一步,是每個學生單獨聽寫,像傳統默書那樣;第二步,是讓兩三個學生組成小組,共同討論默寫的文章,可以參考字典、課本,重點是討論必須基於理性,組員要提出理由,解釋或辯護自己的串寫,最後達致共識,將默寫內容謄寫在一張紙上,署上每個組員的名字;第三步,是老師在黑板寫出正確答案,解答學生的疑問。這三個步驟都不涉評估,只是學習。完成「協商式默書」翌日,老師可以朗讀同樣的課文,讓學生默書,這次才正式計分。
英國學校則有另一種玩法,叫「聽寫重組(dictogloss)」:老師朗讀文章,學生只需寫下關鍵詞,然後自己重組文字,寫出來的東西不必跟老師所讀一模一樣,能傳達原文的意思就夠了。這種默書方法貌似創新,我覺得只是復古。早在十二世紀,哲學家伯納德(Bernard of Chartres,其名言就是那句「站在巨人肩上」)已要求學生把前一天聽過的課,用自己的語言重組出來,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如此形容這個教法:「在他們來說,後一日就是前一日的學生(apud eos praecedentis discipulus sequens dies)。」是不是很像現代的dictogloss?
由此可見,古法不一定沒價值,有時候,新到盡頭就是舊。默書要不要廢除,也許不是最有意義的問題,真正應該思考的是:什麼形式的默書才最有效?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
局勢持續演變
與您見證世界格局重塑
-------------------
🔔下載大紀元App 接收即時新聞通知:
🍎iOS:https://bit.ly/epochhkios
🤖Android:https://bit.ly/epochhkand
📰周末版實體報銷售點👇🏻
http://epochtimeshk.org/stores